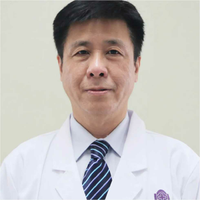
述评:谈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手术理念的转变
(作者声明:本文的任何转载需经作者同意,引用需注明出处)
全文刊登在:杨学军.谈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手术理念的转变[J/CD].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2013,7(22):9825-9827.
一、背景
人类肿瘤的诊治迄今仍是一个难题,当发生在依然未全知的中枢神经系统(CNS)时,无疑又增添了迷惑和复杂。尽管如此,医学理论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不同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先驱们的开拓与医学同仁们努力,还是使CNS肿瘤诊治成为现代医学的一个亮点。从Cushing和Bailey(1926年)依据胚胎残余学说对CNS肿瘤进行系统分类开始,CNS肿瘤病理分类已由WHO主导更新到第四版(2007年),除了精确注释了CNS肿瘤组织病理学特点,还归纳了脑肿瘤发生与发展的基因学特征(genetic profile)。从Dandy发明气脑造影(1918年)和Moniz的脑血管造影(1927年)通过间接影像推断脑肿瘤开始,当今影像学诊断已从明确肿瘤病种深入到尝试对肿瘤亚型的拟诊和肿瘤生物学特性的描述,并直观展示了肿瘤同白质传导束的关系、皮层功能区的定位和肿瘤的分子及代谢信息。从Macewen在英国格拉斯哥肉眼成功实施脑肿瘤手术(1897年)开始,当今显微外科、神经内镜、影像引导等技术攻破了肉眼手术的禁区,促进了“神经功能保护前提下最大限度的肿瘤切除”手术理念的提出。
在CNS肿瘤的临床处理中,是否还有机会对肿瘤进行积极的外科干预这是要首先回答的问题,恶性肿瘤尤为如此,手术切除往往是综合治疗的起始和主要步骤。文献报道,对于未经治疗或治疗后复发的胶质母细胞瘤病人,切除98%或以上的肿瘤组织是具有显著意义的生存预测因素;切除至少78%的肿瘤负荷,才能改善病人的手术结局。当我们在描述切除多少肿瘤才能使病人生存获益时,更多关注的是肿瘤与脑的结构关系及肿瘤的解剖性切除,依据头颅CT和MRI等传统影像所显示的肿瘤自身及与脑结构的解剖细节,在显微手术技术的帮助下,基本可以实现最大范围的切除肿瘤的手术目标。但恶性CNS肿瘤常弥漫浸润性累及脑功能区及深部结构,仅凭上述技术手段和医生的个人经验,使术中的“神经功能保护”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为维持术后神经功能而降低肿瘤切除程度成为了神经外科医生不得已的“妥协”。
从广义上讲,脑重要功能区(eloquent areas)是指维持人类整体功能必不可少的所有皮层区域(包括语言区、运动区、视觉区、以及感觉区)、丘脑及基底节区、脑干和小脑深部神经核团等。在CNS肿瘤手术中对脑功能的保护,主要有三个方面困难:脑功能仍有未知领域、脑功能区存在个体生理差异和CNS肿瘤对脑功能区位置存在病理干扰。
我们以语言功能为例,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们对脑功能还未完全了解。事实上,“eloquent”借用的是拉丁语的“eloquens”,在英文里的对应词汇是“fluent”,亦即语言的流畅。狭义理解“eloquent areas”,就是指能够使人语言流畅表达的脑区。经典理论认为,语言中枢定位于优势半球的Broca区、Wernicke区和角回及缘上回。这些脑区在听音与语义对应、语言理解、词汇表达与发音控制之间的网络协调,构成了Wernicke-Lichtheim-Geschwind模型。但这一模型不能解释一部分复杂失语,对语法、语音、语义等阐述也不足。研究已经发现,Broca区和Wernicke区不是单一功能的脑区,其中可能存在更为精细的功能划分;其他脑区如基底节甚至右侧半球等部位也均参与语言处理;颞上回是一个功能活跃的区域,右侧颞叶至少在言语理解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我们人类语言功能的认识还有很多未知要回答。
除了脑功能区存在生理性的个体差异外,在病理情况下,肿瘤可以扭曲、移位或破坏脑功能结构亦或重塑神经功能。因而,术中依靠传统解剖标志定位功能皮层并不可靠,精确空间定位脑深部病变及与白质纤维的关系也有困难,影响了对累及脑功能区及脑深部肿瘤手术切除的效果。影像引导及神经功能引导的神经外科手术时代的来临,支持我们在CNS肿瘤手术观念上发生转变,即由“在脑组织中对肿瘤进行手术”,转变成“对生长了肿瘤性病变的脑组织进行手术”。上述表述完全不是语序上的游戏,而是需要解决下述技术难题:如何对生长了肿瘤的脑区进行功能评估?如何追踪肿瘤周围的白质传导束走行及脑功能区之间的神经纤维联系?如何实现术中的实时引导?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在CNS肿瘤手术治疗的临床实践中,已率先践行转变手术理念。
二、肿瘤累及脑区的术前功能评估:
(1)任务态功能MRI(task-based functional MRI)是以脱氧血红蛋白的磁敏感性效应为基础,在MRI检查时,受试者完成相应的功能任务(运动、感觉、情绪和认知等大脑激活测试),与血氧水平依赖性功能MRI(blood oxygen level dependent functional MRI,BOLD-fMRI)的基线信号对比,分析判断运动、感觉、语言和视觉皮层区功能,定位标识在MRI图像上。
(2)静息态(resting-state)fMRI是在无刺激或任务激活的静息状态下,测量BOLD信号自发的低频波动,采集大脑自发神经元活动,研究不同脑区的同步激活来反映脑的功能构筑。静息态fMRI可以用于不能配合任务态MRI检查的患者进行皮层功能区定位,如儿童患者、精神症状或药物镇静患者、肢体瘫或失语等神经功能缺失的患者。临床应用研究初步证实,静息态fMRI获取的运动皮质与任务态fMRI、直接皮质电刺激结果类似。
(3)经颅磁性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是一种非损伤性的方法,用于顶叶肿瘤术前运动皮层的功能定位。导航经颅磁性刺激技术融合了经颅磁性刺激、肌电图和神经导航的原理。在神经导航的帮助下,受到经颅磁性刺激并引发肢体肌电反应的确切皮层位置可被记录下来,用于指导运动区肿瘤手术的安全切除。
三、术前纤维束示踪成像
纤维束示踪成像依赖于各向异性来测量沿白质纤维束的水扩散的方向性,并产生一个三维图像直观显示出皮质脊髓束、弓状束和/或视放射等白质内的关键纤维束,可以反映肿瘤对纤维束的压迫、推移或破坏,是评估肿瘤累及白质纤维束的一种较可靠方法。纤维束示踪成像还可以帮助分析,我们感兴趣的脑区之间的神经纤维联系,以及在手术路径上皮质下神经纤维的走行。
四、术中影像及神经功能的实时引导
(1)多模态医学影像的三维融合:术前获得的CNS肿瘤及脑结构与功能图像可以进行融合重建,以三维可视化方式显示CNS肿瘤影像、颅内的动、静脉血管系统、脑功能区的位置、白质纤维束的走行及与肿瘤的毗邻关系。核磁共振成像信息也可以和PET-CT所提示的代谢影像进行同步融合。计算机所创建的三维立体的虚拟现实环境,可以帮助神经外科医生术前制定手术计划,三维可视化定位拟切除的肿瘤靶标并选择最适合切除方式。多模态三维神经导航技术还可以在CNS肿瘤手术中提供交互式动态信息反馈,指导医生在三维影像引导下实现脑肿瘤手术的微创理念。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三维影像引导的图像是以术前影像资料为基础的,所以交互式信息反馈并不能反应术中实时的影像。由于硬膜的开放、脑脊液的流失、病灶的切除所造成的脑漂移将影响这项技术的可靠性。
(2)唤醒手术与直接电刺激:在唤醒手术中,病人在清醒状态下,接受皮质电刺激,根据在感觉区和运动区会造成兴奋性效应,在语言去和记忆去会造成抑制性效应,完成脑功能的定位,标记脑功能图(brain mapping),是脑功能区定位技术的金标准。唤醒手术结合直接电刺激,还可以在术中识别纤维束走形及功能区的皮层下神经纤维联系,实现在脑胶质瘤切除术中脑功能皮质及皮质下功能通路的精确定位和实时保护。
(3)术中核磁共振成像(intraoperative MRI, iMRI)由于能够在术中对病人进行MRI扫描,克服了应用术前影像资料进行神经导航易出现脑漂移的缺陷。医生可以iMRI扫描结果,术中分析肿瘤切除程度及潜在的神经功能影响,并判定是否需要继续切除。iMRI还可以早期发现术中并发症,如出血、脑室梗阻和脑缺血,并及时处理。
(4)术中超声检查:在CNS肿瘤手术中,术中超声与神经导航系统整合,可以对肿瘤、邻近的脑室和肿瘤外周血管进行较好地定位和呈现,显示脑肿瘤的实时影像,引导手术切除。术中超声同iMRI比较,还具有设备费用低、使用灵巧方便、检查时间短、污染机会少等优点。
(5)荧光介导的CNS肿瘤手术:病人口服5-氨基乙酰丙酸(5- aminolevulinic acid, 5-ALA),5-ALA通过血红素合成途径代谢成带荧光的原卟啉IX。高级别胶质瘤中积聚原卟啉IX而正常脑组织中含量非常低,借助于发射波长为400 nm蓝光手术显微镜,可以在蓝色的脑组织背景中,识别红色的肿瘤组织,同其他影像和神经功能实时引导技术结合,有利于肿瘤的识别切除及神经功能的保护。
医学是个动态发展的学科,从CNS肿瘤手术相关技术的发展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临床医生是CNS肿瘤诊治的实践者,我们唯有时刻关注CNS肿瘤研究和转化医学的进步,不断更新自己关于CNS肿瘤诊治的理论与技术知识,认真把握CNS肿瘤诊治原则,才能将CNS肿瘤的诊治提高到新水平,最终惠及病人。
本文是杨学军版权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本文仅供健康科普使用,不能做为诊断、治疗的依据,请谨慎参阅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