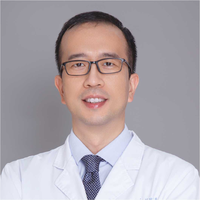 三甲
三甲
窠囊理论在恶性肿瘤治疗中的应用
恶性肿瘤是我国居民死亡主要原因,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近年来,手术、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治疗方法不断完善丰富,但恶性肿瘤死亡率并未得到改善。针对目前恶性肿瘤治疗有效率的“瓶颈”问题,如何深入挖掘中医药理论精髓、拓展中医治疗思路、发挥其特色和优势,是需要不断思考和努力践行的问题。笔者结合个人临床实践,分析中医“窠囊”理论在恶性肿瘤治疗中的应用,现简介如下。
1.窠囊学说的形成与发展
“窠囊”一词,首见于宋代许叔微《普济本事方》,书中作者记述了以单药苍术治疗自身“膈中停饮”宿疾的经历,并提出“湿痰、痰饮成癖囊”[1]。朱丹溪的《丹溪治法心要》引用许叔微的论述,“用苍术治痰饮成窠囊,行痰极有效,痰挟瘀血,遂成窠囊”,在原有“癖囊”之说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明确提出痰瘀同病的“窠囊”理论。分析朱丹溪的描述,可知窠囊的产生是一个缓慢、渐进,由轻而重的过程,痰瘀互结是积聚、肺胀、手足麻木等多种病证的重要病机。后代医家对窠囊理论又有不断完善和发展。喻嘉言《寓意草》云:“至于窠囊之痰,如蜂子之穴于房中,如莲子之嵌于蓬内,生长则易,剥落则难”、“而肺中之窠囊,实其新造之区,可以侨寓其中”[2],形象的描述了窠囊的病位概念。何梦瑶《医碥·杂症》云:“有形之积,阻碍正气,故痛也,而亦有不痛者,日久则正气另辟行径,不复与邪相争,或邪另结窠囊,不碍气血隧道之故,此为难治,以药不易到也”[3],认为痰、瘀、食等有形之邪结聚一处,可不与正气相争而另成窠囊,虽不伴疼痛,反更为难治。林珮琴《类证治裁·痃癖癥瘕诸积论治》曰:“痛犹通连气血,不痛则另结窠囊”[4],指出窠囊之为病,亦可不出现疼痛。唐容川在《血证论》中对“血水相关”、“痰瘀同源”理论有详细论述,“痰水之壅,由瘀血使然,但去瘀血则痰水自消”,“病血者,未尝不病水;病水者,亦未尝不病血也”,因而“治水即以治血,治血即以治水”[5]。痰、瘀均为人体阴液失于正常输布的病理产物。中医素有“津血同源”之说,津、血二者属阴,必赖阳气方得生化、循行,若人体脏腑功能失调、气化失常,肺失治节,脾失健运,肝失疏泄,肾气亏虚,则津液代谢障碍、水湿停聚成痰,血行淤滞或血溢脉外为瘀,痰瘀又可互为因果,此二者胶结停滞,而成窠囊。
2.窠囊的临床症状
痰之为病,随气升降,无处不到,遍及周身内外,五脏六腑,因此窠囊可遍布人体各个部位,症状繁多,会出现呕吐、噎膈、肿物、咳嗽、肢体麻木等一系列临床症状。朱丹溪《局方发挥》曰“遂成窠囊,此为痞,为痛,为呕吐、噎膈、反胃之次第也,饮食汤液,滞泥不行,渗道蹇涩,大便或秘或溏,下失传化,中焦愈停”[6],提示痞满、疼痛、呕吐、饮食不化、大便不调等诸多症状均可能与窠囊相关,上述症状在食管癌、胃癌、肝癌、胰腺癌、大肠癌等消化系统肿瘤十分常见,许多晚期肿瘤患者亦常伴有上述症状,可从窠囊入手论治。窠囊结于一处,局部多形成肿块固定不移,或为瘿瘤瘰疬、或为症瘕积聚,正如《内经》云“汁沫与血相搏,则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积成矣”。《丹溪心法》云“肺胀而嗽,或左或右不得眠,此痰挟瘀血碍气而病”,痰瘀胶结于肺,阻滞气机,宣降失司,可见咳嗽痰多等症,且顽咳、喘息缠绵难愈。此外,窠囊还可出现肢体麻木失用,痰夹瘀血,流注经络筋骨,阻滞气血循行,不能荣润肌肤筋脉,可出现肢体麻木,甚则有如中风,手足麻木偏废。
窠囊者舌质多紫暗,或伴瘀点、瘀斑,舌苔多白厚而腻,内有蕴热则苔黄,此类患者多属阳虚体质,可见舌体偏胖,边有齿痕。脉或弦、或滑或涩,痰偏重者多见滑脉、弦脉,偏瘀者常见涩脉。
需要提出的是,疼痛是窠囊的重要临床表现,《张氏医通》云“痰挟瘀血,随气攻注,流走刺痛。”何梦瑶和林珮琴均提及窠囊已成而不伴疼痛的情况。痰、瘀为有形之邪,相互胶结与正气相搏则有疼痛;窠囊已成也可不阻碍正气,“正气另辟行径”不与邪争,药力难达病所而疾病难治,该理论对恶性肿瘤中医诊疗颇有可借鉴之处。一方面,部分体检发现的恶性肿瘤患者,在确诊时没有任何明显症状,中医辨证往往难循主症以蔓引株求,用正气不与邪争可做解释,以痰、瘀二字为眼目着力辨证。另一方面,窠囊之邪不阻碍气血循行、不出现疼痛时,药力往往难于直达病所,治疗难度更大,医者不可不察。
3.窠囊的临床特点
恶性肿瘤症状多端、病位广泛,病程迁延、治疗难度大。痰瘀互结见于恶性肿瘤者,又与日常咳嗽、跌打损伤所见之痰、瘀不同,乃顽痰、死血日久不散,蓄而化毒,痰瘀毒胶结、凝滞不化而成窠囊,尤其具有顽固性。朱丹溪谓“痰病久得涩脉,卒难得开,必费调理”;喻嘉言谓“任行驱导涤涌之药,徒伤他脏,此实闭拒而不纳耳。究而言之,岂但窠囊之中,痰不易除,即肺叶之外,膜原之间,顽痰胶结多年,如树之有萝,如屋之有游,如石之有苔,附托相安”。痰瘀互结胶固难化,使得病程迁延难愈。恶性肿瘤治疗周期较长,多为久病难愈、重病难治者。此类患者又见窠囊之证,应充分考虑痰瘀互结的病理因素,治疗兼顾痰瘀。对于痰病治痰或瘀病治瘀久不获效者,也应参考窠囊理论,从痰瘀毒胶结入手来辨证。
现代医学研究认为,实体肿瘤的增长和癌细胞的不断增殖,与细胞外周间质中的新生微血管密切相关,种类繁多的酶和生长因子参与癌细胞的分化、发展、免疫调控(逃逸),肿瘤细胞的微环境对于癌细胞的转移和扩散至关重要。这与窠囊理论在某些方面相契合,在某个特定部位、痰瘀毒胶结凝聚成形、或与正气相搏或不与正气相争,该病灶的形成既离不开患者的体质大环境,又对体内其余部位产生后续影响,具有迁延性、顽固性。因而如何有效化解痰瘀毒胶结之窠囊,对于恶性肿瘤治疗十分重要。
4.治则治法
对于痰挟瘀血之窠囊,朱丹溪主张“导痰破瘀”的治疗大法,以导痰汤配合化痰、活血的药物,痰瘀同治。《丹溪心法》云“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证治汇补》云“痰挟痰血,结成窠囊者,宜逐瘀行气”[7]。《医宗金鉴》云“痰积流注于血,与血相搏。。。当以散结顺气、化痰和血”。气为血帅,气行则血行,气能行津。气机调畅与否,是贯穿窠囊形成、发展全过程的关键因素。窠囊的治法以调气化痰、破瘀解毒为主。肿瘤患者体质多属阳虚寒凝,当配合补肾温阳之品,益火之源以化寒痰瘀毒;少数从体质热化或局部病邪郁久化热者,又当辅以解毒凉血之味,清化毒热。调理气机,尤需注重肺脾肝三脏。肺主气、朝百脉,主宣发肃降,又为水之上源。脾主运化水湿,位居中焦,为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既主生血又能统血。肺脾两脏均与气、痰、瘀三字丝丝入扣。肝藏血,主疏泄,调畅一身之气机,通而不滞、散而不郁;又“肝主谋虑”,调节情志舒畅、血气平和,与气、瘀二字紧紧相扣。且肿瘤患者多兼肝失条达之证,疏泄不及则抑郁寡欢、多愁焦虑,疏泄太过又见烦躁易怒,每从肝气入手可取效。
尤在泾《金匮翼》云“盖人之气血得温则宣流也,及结而成坚癖,则兼以消痰破饮之剂攻之。消者,损而尽之”,指出破痰瘀、化坚癖,当消损而尽之,其中“损而尽之”四字发人深思。窠囊既成,难以速解,肿瘤之病,更须持久用药。损而尽之,内含持久之意,水滴石穿,善于守方,久久方可消散痰瘀。肿瘤患者术后病灶虽除,但痰瘀互阻、气机不畅的体质状况难于立即改善;放化疗后,病情虽暂时稳定,窠囊之势犹存,更不可静待其变,均可在扶正固本的同时,调气化痰、破瘀解毒,损而尽之。关幼波认为:“治痰必活血,血活则痰化;治血(瘀)必治痰,痰化血易行”[8]。窠囊理论提示了恶性肿瘤发展变化过程中,痰湿、瘀血二者之间互为因果、互相搏结、彼此影响的密切关系,对于正确认识恶性肿瘤这类顽固疑难病证的病因病机,开拓新的的治疗思路和方法提供了理论根据。
5.窠囊治疗常用药物
5.1苍术 辛、苦、温,主入脾、胃两经,气味辛烈,健脾、运脾之功殊胜,又能燥湿化阴邪,《成方切用》谓“水饮结成窠囊,非苍术辛烈雄壮,不能破之”。苍术性走而不守,通彻三焦上下,为治疗窠囊之痰的要药。
5.2五灵脂 苦、甘、温,主入肝、脾经,生用行血止痛,炒用止血。《神农本草经疏》谓其“凡心胸血气刺痛,妇人产后少腹儿枕块诸痛,及痰挟血成窠囊,血凝齿痛诸证,所必须之药。”[9]五灵脂破血行血、化瘀止痛,兼有理气祛风之功,善治血气刺痛,用治窠囊颇为合拍。
5.3白芥子 辛、温,主入肺、胃经,利气豁痰、通络消肿止痛。《本草求真》言白芥子“以辛温之性搜剔胁下、皮里膜外之痰”,则“无阻隔窠囊留滞之患矣”[10]。白芥子味厚气轻,兼具辛散之力、搜剔之性,开导之力强而不甚耗气,寻常化痰药物药力难以直达之处,非白芥子莫能达。
5.4威灵仙 辛、咸、温,主入膀胱经,祛风湿,通经络,消痰散积。《药品化义》谓其“性猛急,盖走而不守,宣通十二经络,主治风湿痰壅滞经络中,致成痛风走注,骨节疼痛,或肿,或麻木。风胜者,患在上,湿胜者,患在下,二者郁遏之久,化为血热,血热为本,而痰则为标矣,以此疏通经络,则血滞痰阻,无不立豁。”威灵仙疏利之性强,善于消散积湿停痰、血凝气滞,气虚者不可久服。
5.5竹沥 甘、苦、寒,主入心、胃经,清热滑痰、镇惊。《本草衍义》云“竹沥行痰,通达上下百骸毛窍诸处,如痰在巅顶可降,痰在胸膈可开,痰在四肢可散,痰在脏府经络可利,痰在皮里膜外可行”。《时方妙用》谓“以竹沥姜汁,可以透窠囊也。然内之浊痰,荡涤虽为得法,又必于潜伏为援之处,断其根株”[11]。竹沥遍走经络,搜痰结,甘寒又能益阴除热,与姜汁合用则化痰之力殊胜。
5.6水蛭 咸、苦、平,有毒,入肝、膀胱两经,破血逐瘀,通经脉,利水道。张锡纯盛赞水蛭,言其功效破瘀血而不伤新血,专入血分而不伤气分,且主张宜生用,忌火炒或油炸。生水蛭腥味重,可研细粉后装空胶囊吞服,每次2-3g。水蛭逐瘀血、恶血,破坚消积而不伤正,善解痰瘀胶结日久之窠囊。
6.验案举隅
程某,女,54岁,2010年确诊滤泡型淋巴瘤,反复多程化疗后,持续III度骨髓抑制,白细胞、血小板减少,无法耐受化疗,转求中医治疗,初诊时间2015.3.6。主诉:神疲乏力,下肢无力,口干口苦,食欲不振,晨起咯白粘痰涎,大便粘滞不爽,夜眠安,右颈部可及约2cm大小包块,皮色不变,质硬,压之无痛,舌质紫暗有瘀斑,苔薄白、中有裂纹,脉沉弦,重按无力。证属痰瘀胶结,蕴久化热,耗伤气血,脾肾不足,治以化痰解毒、破瘀散结,益气健脾。处方:水蛭12g、守宫9g、赤芍12g、白芥子9g、浙贝母20g、生黄芪60g、海蛤壳20g、威灵仙15g、鸡血藤40g、昆布30g、制鳖甲20g、香附15g、法半夏12g、生薏仁30g、炒白术12g。服用14剂后,患者体力较前改善,颈部包块略软,白细胞、血小板水平有所升高,后以上方为基础,辅以蜈蚣6g、夏枯草30g、生牡蛎30g、僵蚕12g、熟地15g、枸杞15g等药味加减,随访至今,病灶持续稳定。
按:本例患者就诊时病史已近五年,历经多程化疗,白痰、大便粘滞为痰湿之表象,舌质紫暗、兼有瘀斑为血瘀之明证,颈部肿块质硬不移即为痰瘀互阻、顽痰死血胶结成窠囊之处,乏力明显、脉沉且重按无力提示正气已疲,治当紧扣病机,攻补兼施,化痰解毒、破瘀散结,益气健脾并行。处方以水蛭、守宫、赤芍活血逐瘀,白芥子、法半夏、海蛤壳、浙贝母寒温并用、化痰涤痰,威灵仙、昆布、鳖甲软坚散结,生黄芪、鸡血藤、炒白术、生薏仁益气健脾养血,重用香附理气开郁。化瘀药与化痰药配伍应用相辅相成,可以增强散结解毒之功,有利于癌瘤稳定、缩小,但该类药物多属峻烈祛邪之品,易损伤正气,且患者正气已亏,须配合益气扶正药物,重用生黄芪、鸡血藤等药,标本兼顾,扶正祛邪,乃得良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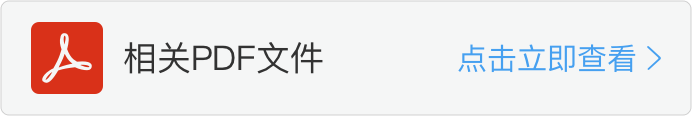
本文是叶霈智版权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本文仅供健康科普使用,不能做为诊断、治疗的依据,请谨慎参阅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