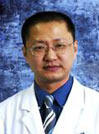 三甲
三甲
特发性肺动脉高压的外科治疗:疗效可媲美“肺移植”的POTTS分流术
特发性肺动脉高压是一种并不罕见的罕见病,而且目前治疗手段仍然较为有限。以靶向药物为核心的“Advanced Therapy”是目前控制特发肺动脉高压症状的主要手段。但在药物治疗基础上,是否有新的手段去遏制肺高压的进展,去提高患者的生存和生活质量呢?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是中国接诊儿童肺动脉高压最多的中心之一,我们一直在思考,在开拓这个领域的治疗手段,希望能给处于“绝望”之中的肺动脉高压的孩子和家长带来些许新的希望。
下面是我们中心新近发表在《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的一篇文章,这可能是国内第一例利用POTTS分流术治疗儿童重度特发性肺动脉高压的报道。现摘录如下,期待和患者家属和同行们更多的交流,一起努力去普及此术式。
急诊Potts分流术治疗儿童特发性重度肺动脉高压一例
张浩,等.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2021,49(6): 621-623. DOI: 10.3760/cma.j.cn112148-20200803-00612
患儿男,3岁6个月,因“纳差、乏力一月余,发现肺动脉高压半月余”入院。患儿身高110 cm,体重14 kg,入院前半月余因肺动脉高压危象症状确诊为特发性肺动脉高压(idiopathic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IPAH),接受降肺动脉压力口服药物(西地那非、波生坦)等治疗,病情趋于稳定后转至我院。我院复查超声心动图提示右心房、室明显增大,房间隔和室间隔偏向左侧。心脏增强CT及磁共振成像(MRI)提示右心房、室扩大明显,右心室收缩功能下降,右心室射血分数34.4%,右心室舒张末期容积107.88 ml/m2(图1A、C)。入院后全麻下行心导管检查术,导管检查测定降主动脉压力为108/59 mmHg(1 mmHg=0.133 kPa),肺动脉压力为88/42 mmHg(肺动脉体循环压力比值0.81),降主动脉氧饱和度99.6%(吸氧下),肺循环血流量/体循环血流量(Qp/Qs)=1,肺血管阻力指数(PVRI)=14.40 Wood单位,肺血管扩张试验阴性。导管检查结束拔除气管插管后吸痰过程中患儿心跳突然下降至50次/min,外周动脉搏动未触及,考虑发生肺动脉高压危象,立即再次行气管插管并予以心肺复苏后转送至重症监护室(ICU)。
入ICU后经充分镇静、强心、加用曲前列尼尔静脉注射,并经右侧颈内静脉置入肺动脉漂浮导管监测肺动脉压力,患儿病情基本平稳,但吸痰时仍易出现肺动脉压力明显升高。二次气管插管拔除后,均因躁动或吸痰而发生肺动脉高压危象需紧急气管插管。在术前ICU监护期间,漂浮导管监测下肺动脉压力波动于130/81(98)mmHg和76/33(50)mmHg之间,脉搏连续心输出指数(PCCI)波动于3.0~5.2,肺动脉压力体循环压力比值波动于0.69~1.34。术前药物治疗方案为米力农0.5 μg·kg-1·min-1、曲前列尼尔30 ng·kg-1·min-1,并口服波生坦和西地那非,常规利尿,瑞芬太尼充分镇静。
患儿为IPAH,经过波生坦、西地那非和曲前列尼尔三联降肺动脉高压药物规范治疗后,肺动脉压力下降不明显,易发生肺动脉高压危象,遂行体肺动脉连接术(Potts手术),在右侧颈动静脉插管体外循环辅助下进行。在颈部插管后实施体外循环,然后患儿右侧卧位,于左后外侧第4肋间进胸。经左肺叶间裂游离左肺动脉主干以及左上、左下肺动脉分支,肺动脉分支放置控制带。术前心脏增强CT提示降主动脉直径为10 mm,因该患儿在充分镇静和三联药物治疗时肺动脉压力可降至体循环压力以下,因此采用8号Gortex管道,以期起到限制性分流的作用。肺动脉吻合口位于左上肺动脉近端,降主动脉上吻合口为距离肺动脉吻合口距离最近的位置(图2)。关胸后于手术室即撤离体外循环装置。手术结束后吸入浓度为21%的氧气的情况下,患儿上肢动脉血氧分压为85 mmHg,下肢为70 mmHg。术后2 h停用曲前列尼尔,术后19 h撤离呼吸机,术后6 d回普通病房。术后上肢经皮氧饱和度维持在82%~100%,下肢维持在69%~100%,上下肢氧饱和度阶差2~14。
出院后患儿口服波生坦和少量利尿剂。分别于出院后半个月和3个月进行电话随访,患儿无晕厥、青紫、乏力、活动受限,世界卫生组织(WHO)心功能分级Ⅰ级。术后1个多月门诊复查,超声心动图提示在静息下Potts分流管道双向分流,左向右为主,分流速度1.67 m/s,经三尖瓣估测肺动脉收缩压为79 mmHg,MRI提示右心收缩功能改善、左心室受压明显改善,右心室射血分数37.0%,右心室舒张末期容积86.00 ml/m2(图1B、D)。静息时下肢氧饱和度为85%~93%,上肢为97%~100%,上下肢氧饱和度阶差约为10。
讨论
IPAH预后极差,目前治疗手段非常有限。20世纪90年代IPAH患儿中位生存时间仅为10个月[1],即使在靶向药物治疗时代其5年生存率也仅为50%~80%[2]。若患儿因为地区或经济因素等的限制无法接受持续静脉泵入前列环素类药物其中位生存时间仅为4年左右[3]。除了肺脏移植,经房间隔造口是IPAH外科治疗的手段之一。但房间隔造口术可能造成全身缺氧,不利于儿童生长发育,而且造成的瘘口容易自行闭合而使手术失败[4,5]。因此,通过连接主动脉和肺动脉的Potts分流术成为治疗IPAH或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术后艾森曼格综合征的一种新选择[5]。Potts分流术不会造成上半身缺氧,有助于保证脑和冠状动脉系统氧供,并且大动脉之间的分流管道可以产生较为大量的分流,从而快速降低右心室压力。因此Potts分流术治疗IPAH也被纳入治疗指南中[6],但目前尚未见国内相关报道。
围术期肺动脉高压管理是Potts分流手术成功的关键。Baruteau等[4]的研究中24例儿童接受肺动脉高压Potts分流术治疗,多数患儿术前就接受了极其严格的三联靶向药物治疗,且术后多数患儿仍需二联靶向药物长期口服维持。本例患儿在肺动脉高压危象发生后接受了三联肺动脉高压靶向药物治疗,而后进行了外科手术。同时,需强调要在围术期放置肺动脉漂浮导管,动态观察肺动脉压力变化,便于围术期管理。本例患儿在三联药物治疗和充分镇静的前提下,肺动脉压力最低可达体循环压力的69%,麻醉下行心导管检查时肺动脉压力也低于体循环压力(肺动脉体循环压力比值0.81),但一旦躁动肺动脉压力就急剧升高,最高可达体循环压力的1.34倍,从而使得拔管屡次失败。为了避免Potts分流术后血液由主动脉向肺动脉“倒流”,有学者认为术前肺动脉和体循环压力之比至少要在70%以上[7]。因此我们认为该患儿存在Potts手术指征,在第3次气管插管后实施了手术。术后随访也显示,手术构建的肺循环到体循环的通路起到了很好的“泄洪”作用。当患儿活动或啼哭时,下肢血氧饱和度会明显下降,但不会出现气促或突发昏厥等“肺动脉高压危象”的临床表现。
对肺动脉高压患儿实施Potts分流术风险较高,因为其对麻醉和开胸操作很难耐受。而且,一旦发生外科性出血则可导致致命性后果。因此,很多中心在开展Potts分流术初期倾向于在体外循环的辅助下实施[8]。在体外循环辅助下,患者的肺动脉压力会随之下降,而且胸内手术操作不会导致肺动脉压力骤增和压迫肺叶而影响肺氧合。但体外循环往往需要血液预充,而且非生理的循环本身会导致肺损伤。因此,后续随着解剖认识的深入和手术经验的积累,我们也将尝试在非体外循环下实施手术。
Potts分流术可选择肺动脉和降主动脉的直接吻合,也可选择一个外管道将其体肺循环进行连接[4,9]。考虑到远期肺移植术,目前多数中心采用外管道连接的方法。在肺动脉压力和体循环压力相近的情况下,可选择略小于降主动脉直径的管道。本例患儿术后超声心动图示管道存在双向分流,Potts分流术后几乎无法避免存在一定程度的左向右分流。因为日常的肺动脉压力水平呈波动状态,因此带瓣膜的单向分流管道可能是更理想的选择[4,9,10]。
由于儿童IPAH预后极差,即使进行肺移植治疗中期存活期也仅为3.6~6年[11,12]。而合并体循环和肺循环分流通道的艾森曼格综合征患者,即使不进行肺移植,也可以存活至中年[13]。Potts分流术某种程度上而言,是构建一个“人工”动脉导管,通过体肺循环之间一个较大的双向分流减少患者对靶向药物的依赖度,延长肺移植等待时间。但是由于面对的是高危人群,目前Potts分流术手术死亡率仍高达15%~20%[4,7,14]。同时,对于右心室功能明显衰竭的肺动脉高压患者,Potts分流术可能无法改善其临床症状和生存率[8]。总之,我们仍需积累经验,加强对患者心功能和肺动脉压力的综合评估,进一步完善围术期处理策略,继续探讨Potts分流术在难治性IPAH治疗中的应用。

图1
患儿Potts分流术前、后超声心动图及磁共振检查结果[1A为术前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示左心室受压明显,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2.45 cm;1B为术后2周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示左心室受压明显改善,LVEDD 3.09 cm;1C 为术前磁共振检查结果,示右心房、室明显扩张,左心室明显受压,右心室射血分数34.4%,右心室舒张末期容积107.88 ml/m2;1D为术后1个月磁共振复查结果,示右心房、室缩小,左心室受压明显改善,右心室射血分数37.0%,右心室舒张末期容积86.00 ml/m2]
图2
Potts分流术图片及其示意图(2A为Potts分流术完成效果;2B为手术示意图;2C为术后CT二维重建显示Potts分流管道)
本文是张浩版权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本文仅供健康科普使用,不能做为诊断、治疗的依据,请谨慎参阅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