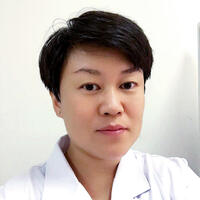 三甲
三甲
医生只看病呢,还是看得了病的人?
当我作为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的一名研究生的时候,在矮小门诊上遇见了一位年轻的“老病人”,她十余年的诊疗之路让我感慨良多,获益匪浅。
这位20岁出头的姑娘因儿时做的颅内肿瘤手术出现了全垂体功能递减,带来了诸如生长发育停止、乏力易疲劳、抵抗力降低等一系列问题。爱女心切的父母带她不远万里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矮小门诊寻求帮助。这份泛黄的老病历中清晰详细地描述了十余年前生长激素等激素的替代治疗方案,还附上了一份当年接诊的史轶蘩教授写给当地医院的病例摘要。姑娘的父亲回忆说,他的家乡在祖国的大西南,姑娘初病时曾跑过无数个医院寻医问药,幸运的是找到了当时率先应用生长激素治疗生长激素缺乏症的北京协和医院矮小门诊,不幸的是一家人需要常年横跨大半个中国取药随访。史轶蘩大夫为了解决患儿家庭两地奔波之苦,细心周到地写下了这份病历摘要,将生长激素缺乏症诊断的确立、生长激素替代治疗的方案和疗程中需检测的化验指标进行了细致地描述,指导当地医生对姑娘进行随访和后续治疗。姑娘一家人非常感动,小心珍藏了这些年全部就诊的病历资料和票据,当他取出这些微黄的病历,史轶繁大夫的仁心仁术浮现眼前,不仅治好了她的疾病,还把解决整个家庭面临的具体困难当成了医生份内的职责。
如今姑娘回到当年的矮小门诊,接诊她的是与患儿们毫无距离感的亲切的潘慧教授。长大成人的姑娘体型匀称,身高160cm,各项化验指标都达到了正常参考范围。一家人十余年如一日的坚持似乎终于等到了圆满的答复,然而看病的过程真的结束了吗?
父亲在整个就诊过程中,连珠炮一般地将对女儿的种种思虑统统讲了出来,潘慧教授边讲边画,分析解释:“目前的治疗效果非常好,她不再需要大剂量的生长激素刺激骨骼纵向生长,可以调整成小剂量给药方案,以改善体能、精神状态、增加肌肉力量等作为主要治疗目标。”相比于已经替女儿的未来规划好了每一步的父亲,潘慧大夫观察到姑娘本人自始至终表情平淡,一句话都没说。这让潘大夫感到担忧:“也许我说这些话有些重了,但是,我不得不说,您女儿的生活要交给她自己,无论病痛还是幸福,必须让她自己亲自品尝。90%的矮小症患儿都伴随有孤独、社交恐惧、情绪不稳定等心理障碍,现在她在生理上已经具备了回归社会的条件,心理上却因为父母数年如一日的过度关注和操持,难以戒断对家长的依赖。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和行为问题,是整个家庭需要面对的问题,千万不要用一个“病人”的帽子盖住她的一生。”姑娘的父亲有些不好意思起来,用力地点点头,一直没说话的姑娘露出了释然的微笑,这话说到了她的心坎里。
在我们接诊的许多家庭中,父亲确实是存在过度焦虑的情绪,孩子幼年患病,多年需要药物替代治疗,作为父母内心需要承受的压力之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却不是“个例”,在门诊能够遇到很多相似的家长。我们从这个故事中跳出来,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分析一下,他们面对的世界。
许多身材矮小的患儿面临的心理问题是共通的,他们觉得自己是茫茫大海的一叶孤舟,性格孤僻、害怕交往;他们自我封闭现象,不愿热情地投入生活,却又抱怨别人不理解自己,不接纳自己。焦虑、抑郁、恐惧,学业的繁重,未来职业的选择,自身的期望,家庭学校的压力,自我控制情绪能力差都成为他们进步的障碍。由于自身生理上的不足,怕遭同学讥笑而耻于与人交往,产生压抑退缩而变得孤立、离群,同学之间关系较差。然而这个姑娘面临的家长的过分保护,更使得她缺少与他人交往和集体生活的机会,导致其在集体活动和社交能力方面明显落后于同龄人。
我们在治病的过程中不仅仅关注身高,更重要的是维护心理健康,让矮小儿童健康成长。鼓励积极参加集体活动,不要因为惧怕孩子受到伤害和挫折而过度保护,主动和同伴、陌生人交往,在交往过程中,逐渐去掉羞怯、恐惧感,使自己变的开朗、乐观、豁达,融入集体中,尝试各种团队活动,学会合作,真诚待人,建立友谊,鼓励儿童敞开心扉,学会交流和沟通。
无论是幸福感还是成就感,都不是父母能给的,而只能是自己的主观体验。教会孩子接受和勇于面对自己的病痛以及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琐碎事务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所以潘大夫在门诊总是强调,需要皮下注射药物的孩子,一定学会自己完成,这是教会他独立面对困难的第一步。
医学关乎生命,因此多了一丝哲学的意味。但是医学既不是纯粹的科学,也不是纯粹的哲学。它游离于科学与哲学之间,涵盖了社会学、艺术、心理学。如果复杂的医学被单纯的科学取代,是非常可怕的。如果医生只关心病人得病的器官和化验指标,而不关心患病者的痛苦和困惑,以及他康复以后如何回归社会的问题,那么就失去了医学发源的初衷,更不是医学发展的目的。所以医生关心的应该是得病的这个人,关心他真切的痛苦以及社会处境。而不只是患病的器官。
本文是张昱版权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本文仅供健康科普使用,不能做为诊断、治疗的依据,请谨慎参阅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