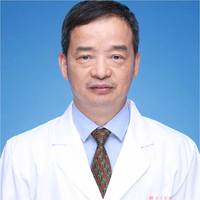 三甲
三甲
董肇杨 | 生而为医,是我最大的幸福(转载自““晔问仁医 ””)
董肇杨
生而为医,
是我最大的幸福

“你到底图什么呢?”这是我反复追问他的一句话,这个拼命退还红包,甚至还自掏腰包动手术的军人,实在是一个另类,他说,什么都不图,就图当下的心安理得,“我在做一件很少有人愿意做的事,不能分心,荣誉和金钱,都容易让人迷失,我不能。” 武警上海总队医院烧伤和创伤修复科主任,主任医师董肇杨,擅于大面积烧伤治疗,大面积创伤修复。 半个脑壳的中年人,从火葬场拉回来的小伙子,生满蛆虫的残肢,百分之八十五烧伤面积的小孩,没了阴茎的下体……我想,这辈子见到最恐惧的画面,是在他的电脑上。他边看边说,我的胃神经却一阵一阵抽搐。 “他们来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没得选择,我也不会推辞,我知道,找上我,是彼此的缘分,我给他们最后的希望,他们成就我完成一件件高难度的作品。” 从头到足,从烧伤到创伤,他的皮瓣创新修复能力巧夺天工,我后来见到了一张张手术后的照片,照片上的人都在微笑,死神已经暂时走开了,他们的躯体不再狰狞,不再触目惊心。 “他们都挺好的,还懂得感恩,出院的时候有跪下磕头的。好多人都是赤贫,我们还得想法子捐款给他们做手术,以及术后康复。”他说。 “我就是个收破烂的,捡到每一件破烂,我都如获至宝,煞费苦心的修复,彻夜难眠的思索,为的是还一个承诺,还一个尊严。”他说。为此,他有时被同行奚落,有时被同事误解,他依然故我,我行我素,特立独行。 这就是他的人生,从江西农村走出,已经在烧伤创伤领域颇有建树的他,常常会梦见一头孤狼,在冷冷的峭壁上长啸,“一次次自我挑战,蛮孤独的,不过我会自我安慰,每完成一次巨大修复,会喝一口小酒,自我得意一番。” 我见到的触目惊心的创口,在他看来早就司空见惯,许多别家医院不收的病人,把他当做最后一根稻草,他说,照单全收,我尽最大的努力治疗。 我问,如果你在瑞金,在仁济这样的平台,你会怎样,他说,人生如棋,落子无悔,每一步都有每一步的意义,每一个平台都有这个平台的宿命,“我在这里,当下很好,我的刀法和创新力得到激发和完善。” 有空的时候,他打网球,慢跑,他说所有的委屈和压力,都会随着汗水,流淌殆尽,人到中年,他说还有激情,只是更有厚重感,高三的女儿用阿黛尔的歌声鼓励他,被他用作手机铃声,每次听到这个铃声,他心中无比满足。 “见过太多死亡了,我认为我们的工作应该有更远大的目标——助人幸福。幸福关乎一个人希望活着的理由。在形形色色的理解里,生命与死亡的尊严形态各异。但尽可能地遵照本人意愿,做出符合内心需求的选择,才是尊严的真意。 ” 我和他聊起我们这个年代的共同记忆,他说极尽疲惫的时候,会找一些老电影温习,“尽管电影是黑白的,但里面的每一个脸蛋都是明媚的,每一副牙齿都是洁白的,每一个衣衫褴褛的人都是温暖的,每一个坏蛋的脸上都是贴着标签的 ,每 一个坚持信仰的人都是忠诚的,每一个女人的心里都是充满希望的,世界可以如此黑白分明,人性可以如此美好,我愿意相信。”

谈话从一个又一个触目惊心的病例开始。 电脑上的照片一张张展示着,患者被烧伤的惨状,看得人心一直揪着。“你怕吗?”我问。“做烧伤医生怎么能怕这个。”董肇杨平静地说。 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把病情用手机拍了,火车上,飞机上,甚至走路、吃饭,就拿出来看,构想手术方案。女儿从来不敢打开他的手机,就怕一不小心看到血肉模糊的残肢断臂。 董肇杨出身江西乡村,从小学习刻苦,高考成绩是县里前十名,被第一军医大学录取。懵懂的他觉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当个治病救人的医生也蛮好的。虽然特立独行的性格,与军校的“令行禁止”有些格格不入,一开始并不习惯,但是这之后几十年,他再也没有脱下过军装,军人的品格融入身体里。现在他和同事去打靶,十发子弹,依然可以打99环。曾经有闹事的病人家属,握着水果刀刺过来,他不假思索一个空手入白刃,夺下刀来,把一场一触即发的流血事件消弭于无形。“这岂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不畏艰险,这就是军人。” 大学毕业后,他曾在沈阳军区235医院做了四年普外科,1993年,“中国肝胆外科第一刀”吴孟超教授在第二军医大学任教,董肇杨心动,想要去考吴孟超的研究生,可惜最终失之交臂。1999年,他在长海医院烧伤科师从陈玉林教授博士毕业,作为人才引进,来到武警上海总队医院。 医院不大,病人也少,科室里十个医生,那年冬季,科里只有5个病人,这是当年的状况。烧伤科涉及到身体的方方面面,需要对多学科的了解。董肇杨正好有做大外科的经验,也更愿意留在临床一线。有人说,“烧伤科是公认最惨的科”,没人愿意做。可是董肇杨坚持下来了,2002年,他37岁时,任烧伤科主任,很快度过了适应期,救治了一个个不可思议的病例,在某些领域,做出了国际创先的成功。

据统计,每年因意外伤害的死亡人数中,烧伤仅次于交通事故,排在第二位,而且在交通事故伤害中,也有大量伤员合并烧伤,当烧伤占全身表皮面积的1/3以上时就会有生命危险。 我国烧伤专业的发展是从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的,主要是治疗中小面积烧伤和烧伤后瘢痕挛缩后期整形的伤员,之后救治烧伤的工作在全国逐步被普及推广。1958年上海瑞金医院成功抢救了被严重烧伤的工人邱财康,这是全世界第一次治疗烧伤面积超过80%的病例。如今我国烧伤治疗水平已经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欧洲顶尖权威专家曾在公开著作中表示:烧伤科和断肢再植,是中国医生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每一年,董肇杨都能收到十几面锦旗,他都默默收起来,他不愿以此对外炫耀。但他的诊室的墙上,的确也挂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的是“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几个字,普普通通,平淡无奇。然而在这面锦旗的背后,有一个传奇故事。 那是个29岁的年轻人,出了严重车祸,颅骨骨折,颅内血肿,硬膜下血肿,硬膜外血肿,蛛网膜下腔出血,骨盆骨折,左胫骨骨折,肾功能衰竭,脓毒症,皮肤广泛撕脱伤……在某大医院医生抢救了十几天,无力回天。最终,病人被送到殡仪馆,准备火化安葬。可是,躺在殡仪馆柜子里,他竟然又顽强地活了过来,发出了声音。亲人们又惊又喜,马上送到医院继续抢救,此后辗转到董肇杨手里。 这么重的病人,在别人眼里,接下来实在有些傻。面对家属的误会和同事的不理解,董肇杨不顾别人的眼光,争分夺秒把手术做完,为病人争取生存的时间,之后整整四个日夜没合眼,在重症监护室看护病人。幸好苍天不负,最终抢救成功。病人出院的时候,送了他这面锦旗。 这个病例在国内烧伤界被传为一段传奇,全国的几家大医院邀请他专题讲座。面对台下的大主任,甚至院士们,董肇杨丝毫不怵,他说,当初之所以肯接下来这个病例,不为名,也不为利,也许很多人碰到了会回避,可是自己会往前冲。“人活在世上,就要做些有意义的事,每次和这样的病人接触都是一种缘分,也是一次锻炼机会。放弃很容易,但是一个医生想要成就自己,不能见到困难就绕路而行。就像登山运动员一样,登顶的喜悦只是一瞬,山外有山,更高的山峰等待着挑战。”

曾经有一个青海玉树的车祸病人,前期手术情况非常糟糕,很多大医院都感到棘手,最终又到了董肇杨的手里。他之前没有见过类似病例,却也不拒绝。病人的气管被切开,说不出话,他思考了很久,和妻子一起研究解剖结构,最后设计了一个疤痕皮瓣,但是皮瓣裂开,又巧妙地在病人头下多垫了一个枕头,把一个不可能的病例救过来了。这个病例中,董肇杨说,重要的是对解剖的重视。 一位老师曾经告诉过董肇杨:“外科医生最基本的两个素质是,扎好血管,熟悉解剖。”董肇杨牢牢记住了。所以他对于解剖格外重视。2004-2005年期间,他曾多次到尸体解剖室做解剖,了解人体结构,并且参加尸体解剖学习班,拍了大量照片,有空就翻看琢磨。有时碰到非常复杂手术睡不着,他甚至会在半夜里爬起来翻解剖图册。 做这些的原因是,他对生命的尊重。“没有任何一本教科书告诉你所有疾病的治法,在遇到之前没见过的病例,被难住时,到哪里去找答案?到解剖结构里。我把解剖书当做最好的老师。”对解剖的熟悉,让董肇杨手术的时候不会犯错,即使面对被流弹打伤,子弹距离心脏只有一公分的手术,也显得游刃有余。 前几年,有一个乳腺癌手术病人,手术后伤口裂开,迟迟无法愈合,后来被推荐到了董肇杨这里,他巧妙地设计了一个“凸形皮瓣”,一举成功,后来,同类的病人全都来找他;还有过一位84岁的老太太,被公交车压过下肢,下肢骨头很多都外露并坏死了,本来要截肢,被他用自己发明的技术,保住了老人的双腿,老太太86岁的时候,自己一路走来感谢他;一个25年前烧伤95%,被救回来的病人,脚上长了一个很大的肉瘤,需要切除,但是由于身体曾被大面积烧伤,因为下颌与前胸壁粘连而导致头部后仰困难,全身麻醉根本无法插管,后背因疤痕严重并伴有创面也导致腰麻根本打不进去。董肇杨就用一支局麻药,完成了大腿高位截肢手术。后来查文献得知,这样的手术在全国也没有先例,并且在军事和抢险救灾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战争年代或者抗震救灾时期,医疗队必须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抢救伤者,所以这种‘局麻截肢’手术,很有推广价值。” 虽然创先的事物必将带来很多的经济利益,但是董肇杨并没有想将这项成就据为己有的念头,他说,“医疗技术是属于大家的,没有专利之说。希望我的这个病例,能够让更多的生命得到拯救。”

2015年五月,在上海金山区的一个只有两岁的仡佬族女孩,玩耍时掉入滚烫的豆浆锅中,全身烧伤面积超过85%,被辗转送到上海武警医院时,已经生命垂危,处于休克状态,连哭声也没有。 小女孩被安置在烧伤科ICU病房,董肇杨见到之后,也吓了一跳,这是二十多年来,武警医院遇到过的最严重的一个病例。他在旁边守护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带了些小水饺和鸡蛋给孩子吃,没想到,被孩子全部吃光了。 小女孩强烈的求生欲望,给了董肇杨救治的信心。武警医院之前救治过的烧伤孩子,烧伤面积最大的是70%,烧伤面积越大,供皮区就越少,难度会成倍增长。经过大家反复商讨,最终拿出了治疗方案。为了减少小女孩的痛苦,医院将清创植皮手术减少到3次,烧伤科几乎全员上阵。 难度如此大的手术,费用无疑是个天文数字,但是董肇杨说,“当时就一个念头,先救了再说,费用再想办法。”他在家里跟女儿提起,女儿说,“我们来捐款吧。”自己首先捐出了一千元。后来经过电视台的报道,本院医护人员和社会各界人士自发伸出援手,加上医院的减免,将小女孩的手术费用凑齐了。104天,前后三次手术,最终小女孩顺利出院。 这个病例也是中国医生治烧伤的新高度。董肇杨记得,二十年前德国弗兰堡大学的一位大外科主任,见到一例80%成人救治成功时就感叹说,你们中国医生治疗烧伤真了不起!如今这么2岁的小孩,面积达到85%竟然也能救活,不知他知道后该怎么说? 董肇杨坦言,很多手术都非常棘手,他就像是“捡破烂”一样,捡起一个个别人不愿意碰的手术,当做自己最珍贵的宝贝。这些病例中,病人的家庭大多贫苦,可是即使再付不起钱,他也不会把病人往外推。他说,人生在世,生而为医,能够救死扶伤,是最大的意义所在。他这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医生”这两个字。









采访报道日期:2016年11月22号
董肇杨主任于2020年8月1号从部队退休后,现入职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希望在新的岗位为更多的患者服务!
本文为转载文章,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本文仅供健康科普使用,不能做为诊断、治疗的依据,请谨慎参阅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