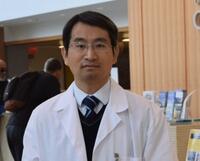 三甲
三甲
美国杜克中国医学学者协会成立
杜克中国医学学者沙龙--新的一年再会

2015年2月8日,杜克中国医学学者沙龙第5期如约而至。本次沙龙走上了清纯路线,看到主持人了吧,我就不用文字赞美了:河北省人民医院的李庆霞和北京肿瘤医院的康晓征。讲者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天坛医院的李子孝和来自杜克大学临床研究中心的居美华人教授冼颖,讲座题目:如何提升临床研究质量;如何撰写医学论文。当我们国内还在争论临床和科研的取舍时,还有些临床医生以各种心态鄙视科研时,我只能说:我们一直都OUT了。
当我们面对信息网络发达到无孔不入的时代,面对先进的科技已将地球上的任何远的地方都缩小在指端和键盘之间,如果一个临床医生还在坚守着自己个人的医学经验而忽视这个大数据时代所带来的冲击;当我们还在固执地认为搞科研就是关在实验室里玩弄几年蛋白、基因和细胞发几篇无关痛痒的文章,尤其认为西方的科研和我们就是仪器设备的区别,也不过是诸如此类的话,我只能说:我们真的OUT了。
李子孝医生所讲的新天坛,新理念,要在以后的发展中让天坛的科研水平超过临床水平。这是给了所有意识到科研力量的同胞们一剂强心针,我们接下来就要双手合十,期望这剂强心针的半衰期无限延长了。当面对美国的小伙伴们谈合作时,唯一一点能让我故作深沉地喝口咖啡,挺起胸膛妥帖地靠在椅背上,直视对方的双眼高昂地甩出杀手锏的是下面这句话:我们中国病例最多。可是当对方提出要我们的数据时,我又傻傻了。我只能说,你们搞那么多医学指南,世界上最大群体的患者不包括在内,这是你们的责任!(怎么感觉有点那个呢?呵呵)当然,我们有了先行者,我们在做,我们还是要乐观地估计未来,因为我们每天的饭局多到气死饮毛茹血的祖先,每天的消费达到了“只选贵的不选对的”的时代,我们日子一天天变好,对未来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当那么帅气的70后冼颖教授登上舞台时,大家还是从沉重的神经压力中转移到眼球吧,男主持人说这是男神,这是很少见的,因为他心中一般只有女神。所以我也不用再仔细描述了,如果照片上你觉得没那么男神的话,请联系摄影师吧,我申请免责。可是当冼老师一张口,我们还需要把重点从眼球转移到沉重的脑神经上,他讲的是如何在顶级杂志JAVA上发表文章的经验之谈啊。这里要再次纠正一下,文章,和在国内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说:你晋升职称的文章够了吗?你文章够报奖了吗?请自行分析其中的含义。冼老师的文章更新了美国卒中急性期治疗的指南,我想这是文章的真正含义吧,患者因此提升了溶栓率,让更多的人得到更切实的治疗。
其实科研的原动力是什么?是一颗保持对大自然界一切的好奇之心啊。我是一名胸外科医生,当我每天打开肺癌患者的胸部时,面对狰狞的肿瘤,我曾经喜欢体会我手起刀落的快感,可是我给患者的只不过是多几年的时间。而且,当一天天过去了,做完一台会有更多的几台等着你,你不觉得要停下来想一想,这是怎么了?那每张坚强的面孔,鲜活的生命,竟不抵一年半载的癌细胞的侵略。一个真正的医者,思考的远不止职业的收入吧?如果真的要想问为什么,请到科研世界来!

喜欢把临床和科研分开来谈的,其实是片面的,或者是被片面的,因为听众要听啊。临床要搞的,很多也是在探索“为什么”的道路上,也是科学的研究,其实原来大家的心思是一样的。大家如果到过发达的国家,用心可以体会到许多,具体是什么呢?你懂的......好吧,如果让我非说不可的话,我确实感觉日本和美国的科研精神值得佩服。无论我参加的实习生、博士、博后的seminar,我都能感觉到大家是一个在科学道路上的group,每个人都会仔细地又时刻能够惊喜地发现脚下这片新大陆的奇异之处,大家在用专注的眼光、认真的态度仔细地搜寻科学之路上的蛛丝马迹,有一种磁性的力量在指引着走向若隐若现的真实世界。
当我们非要自我拷问一番的话,我们还是暂时短浅地归罪于国人的科研素质吧。然而,我们又怎么能做旁观者,我们也是其中的一员啊。这里要提一下我们的沙龙,我们想进步,更希望进步的脚声惊醒沉睡者,每周一期的学术沙龙,带给大家的不知是知识,更是理念和精神。
本期沙龙仍然体现了民主作风,主持人决定的风格,给人有耳目一新的赶脚。好消息很多:沙龙组织正式加入杜克中国学联,名称为:杜克中国医学学者协会。沙龙举办的成功,前所未有,国内教育部麾下门户网站进行采访,我们能做的,只是我们每个人都做一点点,大家的力量才是无限的。中国的春节快到了,沙龙停办两期,3月1日再见,祝每一位看到此文的伙伴们,春节快乐!
本文是李勇版权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本文仅供健康科普使用,不能做为诊断、治疗的依据,请谨慎参阅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