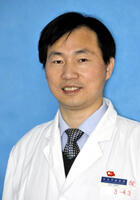 三甲
三甲
中医奇葩在“非洲屋脊”绽放
他是医术精湛的针灸师;
他是热忱无私的青年志愿者;
他是远赴“非洲屋脊”的友谊使者。
中医奇葩在“非洲屋脊”绽放
兆丹 帅东
位于东非高原的埃塞俄比亚,平均海拔近3000米,有“非洲屋脊”之称。去年8月,我国12名青年志愿者远赴那里,开展了为期半年的志愿服务。这是我国青年志愿者首次前往非洲开展志愿服务。
在这12名志愿者中,年龄最大的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39岁的夏淑文。这位有着14年临床经验的针灸师,不仅用精湛的中医针灸技术为病人解除了痛苦,还以无私的志愿者精神谱写了一首中埃友谊之歌。
“中国派来了天使”
到达埃塞俄比亚后,12名志愿者被分到各地,夏淑文来到距首都100公里外的纳兹瑞特市阿达玛医院。夏淑文说,虽然此行之前,自己有了思想准备,但看到眼前的医院,觉得落差还是很大。医院办公楼是二战时意大利的仓库改建的,陈旧简陋。院子没有硬化,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泥坑和积水池。虽然这是埃塞全国第二大城市的州立医院,但规模仅相当于我国差一点的县级医院。
夏淑文到的时候,正是当地雨水多的季节,蚊子、跳蚤到处都是,疟疾流行。夏淑文说,我们认识一位在当地开餐馆的中国老板,他已经患过17次疟疾,我们都叫他“疟神”。
到了医院,夏淑文最着急的是赶快开诊,但是诊室一时无法落实。在焦急中等待了一周以后,诊室被安排到了刚建成的原本作为放射科机房的房间里。
夏淑文搬进去的时候,“装修”的气味很浓。诊室只有一个小窗户,还不能打开通风。夏淑文在屋里养了一盆吊兰,越来越枯,挪到院子里,很久才缓过来。开始,房间没有通电,黑洞洞的,夏淑文只好从隔壁放射科引来电灯。因为想尽早开展诊治工作,尽管有射线辐射的危险,但夏淑文已经很满意了。没有诊桌和诊床,夏淑文就四处搜罗来大小不一的三张诊床。匆忙之中,针灸科就这样开诊了。
其实,在正式开诊之前,夏淑文就开始了救治病人的工作。原来,在筹备针灸科的过程中,夏淑文无意中发现在医院西北角有一家孤儿院,收养被遗弃的儿童。其中有名小男孩叫亚蒂斯,患面瘫已经一个月了,没有得到任何治疗。从发现他的那天起,夏淑文每天上门为他免费针灸。针灸科开诊后,亚蒂斯就转到医院来了。
夏淑文对亚蒂斯很挂念,晚上下了班,还常去孤儿院探望他。每次去,夏淑文都没忘了给孩子们带些零食过去。9月11日,是埃塞俄比亚的新年,夏淑文特意赶过去和孩子们一起庆祝,孩子们兴高采烈,称呼夏淑文是“中国派来的天使”。小亚蒂斯经过近三个月的针灸治疗,面瘫基本痊愈了。
找回失去七年的笑容
针灸科开诊的第一天,来了一位中年人,带着12岁的女儿。小姑娘名字叫碧再特,七年前患了面瘫,留下了明显的后遗症,脸上只有一个表情——僵硬。他爸爸说,已经七年没有看到孩子脸上的笑容了。
听说来了中国针灸大夫,爸爸带上女儿特意从两百公里外的家赶来。为此爸爸向单位请了假,为碧再特办了短暂的休学。爸爸说,诊室还在筹备的时候,父女俩就住在旅馆里等候了。
因为碧再特病得太久了,为加大治疗力度,夏淑文就在针刺的基础上,加用了电针,并配合耳针。由于针灸有一定的痛感,为分散碧再特的注意力,细心的夏淑文特意给她播放MP3听。针灸的同时,碧再特听着优美的中国歌曲,有时竟情不自禁跟着哼唱起来……
十天一个疗程过去了,奇迹出现了:碧再特面瘫症状不断改善。一天,碧再特拿来了她写的日记,上面记录了自己的针灸感受,从用针的个数、针刺的时间、针刺后的感受,点点滴滴都很详细。从日记中,可以看出,碧再特的小脸“一天一个样”:从患侧鼓腮不漏气,到眼泪不再异常分泌;从咀嚼不再疲劳,到微笑时露出了牙齿……
从家里回来后,碧再特的爸爸高兴地告诉夏淑文:周末回家后,家人和邻居们都非常惊讶,觉得碧再特好像变了一个人。脸上有了笑容的碧再特更加漂亮,更加活泼了。每次针灸后,碧再特总是在诊室里不肯回去,为大家表演体操和舞蹈。爸爸还特意花了上千比尔(埃货币名),买了照相机,留下了这些难忘记忆。
第二个疗程结束后,碧再特的脸上还残留轻微的症状,但她的爸爸不得不回去工作了。父女俩向夏淑文告别的时候,留下了详细的家庭住址和乘车路线,盛情邀请夏淑文到他家做客。
夏淑文的精湛医术名声远扬,不少患者从几百公里外赶来进行针灸治疗。病人从最初每天2、3个,到每天有二、三十位患者,其中多数是疑难病、慢性病。为治疗这些疑难病症,除针刺之外,夏淑文使用了多种治疗方法:艾灸、耳针、电针、火针、拔罐、放血等。为增加疗效,夏淑文还开展了特色诊疗项目——按摩治疗,这在国内针灸科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在给病人施完针后等待的间隙,夏淑文就给替病人按摩穴位。夏淑文说,三两个病人按摩下来,累得浑身都是汗。
银针下落祛痼疾
患者兹法是位女警官,今年35岁,患双膝关节炎已经5年了,夜里痛得睡不着觉,走起路来都打晃。兹法来就诊都穿便装,但随身带着枪。夏淑文说:“扎针前,兹法总是趁人不注意,把手枪藏在诊桌最下面的抽屉里,走的时候再别在腰里。”
夏淑文对兹法的病腿施行两次针灸加艾灸治疗后,不见效果。后来,夏淑文决定用火针和放血疗法交替进行。但问题是,这里的病人艾滋病阳性率较高,为避免血液交叉感染,不能重复使用合金材料的坚硬火针,只能以一次性毫针代替。但毫针经火烧之后会变软,要求针灸师操作时不仅动作要快,还要指力适当;否则,不但针身易弯折,而且会增加病人痛苦。夏淑文凭着自己的“指上功夫”,顺利地施行了火针疗法。
放血疗法更不容易,由于医院没有专用的三棱针,夏淑文就去门诊采血站要来了采指尖血用的一次性针。点刺穴位后再拔罐,利用火罐的负压使淤血放得更充分。一个疗程过后,兹法的双腿夜里不再疼痛;两个疗程过后,病人基本痊愈。兹法欢天喜地,不知道怎么感谢夏淑文,干脆扛来一大口袋自家种的木瓜和柠檬。夏淑文回国之前,兹法前来送行,依依不舍,说:“夏医生,留下来吧,我去帮你申请。”
这次,夏淑文从国内带得最多的是一次性的针灸针,一共2万只,分装在两只大纸箱里。走的时候,刚好全部用完。因为埃塞俄比亚艾滋病高发流行,阿达玛医院的住院病人中有许多的艾滋病人。针灸的特殊性使医生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几率更高。针灸直接接触血液,尤其是火针、放血疗法,一旦被感染将是致命的。对夏淑文来说,如果施诊时不小心手指被被针扎破,都存在感染的可能。
为了防止病人间的交叉感染和做好自我防护,夏淑文采取了很多措施:严格消毒,针具都是一次性使用,每个病人更换一次无菌止血钳,扎针和起针都要戴手套。夏淑文说,有时候一个上午下来,带着胶皮手套的双手都被汗水泡白了。
“我的爸爸是夏大夫”
在埃塞俄比亚,夏淑文始终牢记自己不仅是一名志愿者,更是中埃两国友谊的使者。去年11月初,埃塞政治局势非常紧张,发生了动乱。纳兹瑞特市受到波及。但夏淑文仍然坚持为病人诊治,没有停下手中的银针。
这段时间,来就诊的患者小叶希让夏淑文最难忘。小叶希今年10岁,是位活泼漂亮的小女孩,第一次来看病坐在轮椅上。送她来的亲戚介绍说,她是被一家慈善机构收养的孤儿,四个月前出现四肢无力肌肉萎缩,双手不能持物,下肢不能站立。小叶希到各地看过众多医生,打针吃药都不见效果,病例都厚厚的一摞了。夏淑文在为孩子惋惜的同时,暗暗发誓:一定尽力帮助她站起来。上午治疗完毕,中午下班后,夏淑文都推着轮椅把她送回住处。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小叶希病情逐渐好转,不仅能自己穿衣服,还能被搀扶着站起来,后来可以扶墙走几步了。小叶希深深喜欢上了这名来自中国的中医大夫,逢人便说:“My father is doctor Xia(我的爸爸是夏大夫)。”夏淑文说,这是对我付出的最好回报。
阿达玛医院还承担了多个学院的临床教学任务,每天有5-8名实习生到针灸科实习。实习生们对中医和针灸都非常感兴趣,经常问这样那样的问题。夏淑文耐心给予解答,从中医最基本的理论讲起,并结合了病例和临床实际操作,增加了他们对中医针灸乃至中国文化的认识。
在将近半年的志愿服务中,夏淑文累计为病人针灸1530人次,按摩220人次。夏淑文不仅用精湛的医术治愈很多病患,也为中埃友谊以及中医传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正像他在诗中所写的那样:“带来针灸中医,跨越万里传递友谊。正大好年华,弘扬奉献,艰难困苦,披荆斩棘!……”。
本文是夏淑文版权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本文仅供健康科普使用,不能做为诊断、治疗的依据,请谨慎参阅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