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甲
三甲
问诊,临床医生的基本功
洗耳恭听!多听听你的患者的心声!他正在为你提供诊断!
─Rene Laenne
如果你用30分钟接诊一位患者,花28分钟询问病史,2分钟体格检查,不要在头颅X线或脑电图上花费时间。
─Adolph Sahs
在病史采集过程中,追随每一条思路,不要抢先提问,决不给予提示。让患者用自己的话去讲述。
─Wlliam Osler
一、“病家不用开口,便知病情根源 ” 纯属故弄玄虚
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因为肚子痛,母亲带我到公社卫生院看病。那天坐诊的是一位姓王的医生。他非常仔细地问:哪儿痛?多长时间了?开始在哪儿痛?后来在哪儿痛?除了肚子痛,还有别的不好没有等等。最后他又摸摸肚子,开了三天的药,吃过药后,肚子就不痛了。
后来,有人问母亲:找谁看的病?母亲说:找的是王先生。那个人说:哎呀,咋能找他看呢?他是“问先儿”。脸上一副不屑的样子。
所谓“问先儿”,就是问得非常仔细,或依靠问诊诊断疾病的医生。在老百姓中,这是一个针对医生的贬义词。老百姓最相信的是那种仅凭切脉就能诊病的“病家不用开口,便知病情根源”的医生。
我要是将来当医生了,一定不当老百姓看不起的“问先儿”。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早早地埋下了这样的种子。
后来,听说的事就更神奇了:某某医生仅凭切脉可以知道你肝大肋下几厘米,某某医生仅凭切脉可以知道你血压是多少。更有甚者,仅凭切脉可以知道肾病患者尿中有多少红细胞,多少管型。
1965年,我考上了北京医学院。几年后,成了医生。再几年后,成了神经内科医生。再几年后,成了神经病学研究生。再几年后,成了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
在神经内科的医疗生涯中,无论是当进修医师、研究生、主治医师、直到主任医师,一刻也离不开问诊。
后来,在学习中医课程时,才了解到,真正的中医也是非常重视问诊的。有中医十问歌作证:
一问寒热二问汗,
三问头身四问便,
五问饮食六问胸,
七聋八渴俱当辨,
九问旧病十问因,
再兼服药参机变,
妇人尤必问经期,
迟速闭崩皆可见,
再添片语告儿科,
天花麻疹全占验。
于是,我明白了民间流传的“病家不用开口,便知病情根源”,不过是一些人对医学的误解和偏见,或是故弄玄虛,自欺欺人。
海内名医蒲辅周老先生也非常注重问诊。他曾严肃地批评某些医生是“自恃高明,闭目塞听,单凭切脉诊病,哗众取宠,缺乏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科学精神,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态度”。
二、问诊是做一名称职的神经内科
医生的基本功
问诊是任何医生诊断疾病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和程序,更是做一名称职的神经内科医生的基本功。
如果你不知道病人的症状是什么?症状是怎样开始的,性质和严重程度怎样?缓解及加重因素是什么?伴随症状和体征等是什么?诊断将无法开始!
Adolph Sahs老师教导我们:“如果你用30分钟接诊一位患者,花28分钟询问病史,2分钟体格检查,不要在头颅X线或脑电图上花费时间”!
在神经影像三个代表(CT、MRI、DSA)新时代里,一些年轻医生产生出这样的观点:神经病学临床已被减少到试图猜测CT扫描和磁共振成像将显示什么。
被复杂的神经系统定位、定性困扰的神经科医生当然希望这是真的!与其花费长时间去问诊和检查病人,我们何尝不愿通过神奇的机器迅速获得治疗病人所需的所有诊断信息?
遗憾的是,机器不是万能的。新的技术确实意味着我们的诊断医疗设备的巨大进步,但绝不意味着这些能够削弱对正确的临床评估比如问诊的重要性。
诊断头痛的关键是病史。影像设备不能诊断偏头痛、紧张性头痛和慢性每日头痛。大部分的各种头晕病人磁共振扫描也是阴性的。抑郁症焦虑症,以及各系统疾病所合并的焦虑、抑郁状态,CT和磁共振扫描也都无能为力。而这样的病人每天都会大量地涌入神经内科门诊。尽管脑肿瘤及其他病变使神经系统或临近组织的解剖结构发生变形,可以凭借CT或磁共振等做出比过去精确得多的定位诊断。然而,如果这些检查未聚焦于患者症状的责任区,这类病变在影像检查中可不被发现。此外,神经影像可发现与患者目前的疾病无密切关系的解剖异常,但却经常没有临床意义。与X线和脑电图时代相比,神经影像技术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医师必须了解其局限性并合理应用,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作用。
神经系统结构复杂,是由非同源性成分所组成的。其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由具有各种不同外观、功能以及对各类疾病的敏感性各异的多种亚单位所组成。也正是因为这样,神经系统不同部位的病变才会产生能让病人感知和表达出来的症状。而凭借这些症状,我们就能大致定位神经系统病变(如语言障碍、失认和失用、视野缺损、偏瘫、意识、感知或行为改变等──大脑病变;颅神经异常、交叉性偏瘫──脑干病变等等)。
实践证明:根据主诉,是能够做出定位诊断的。
三、清晰与充分的病史的重要性
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份
临床诊断的过程决定于对将要诊断什么的清楚的理解。因此,清晰与充分的病史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份。未获得足够的病史很容易让患者针对实际上并未经历过的症状进行昂贵的、创伤性的、潜在危险的和最终无用的检查。同时,却忽略了必要的和适当的检查。
近年来,神经系统的各种影像学检查方法发展很快。从CT开始,现在已经有了MRI、PET、SPECT、DSA等许多。比起过去的望闻问切,望触叩听先进了许多许多。有许多过去不知道原因的疾病,现在知道了。有许多不知道发病机制的疾病,现在知道了。比如,对于脑血管病,过去中医仅能判断出是中风,或进一步分为中经络,中脏腑。而西医,只能诊断出是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和脑梗塞。而现在,经过检查,仅对脑梗塞,就可以区别为大血管粥样硬化闭塞、心源性脑栓塞、小血管病变和其他原因引起。从而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治疗和二级预防。但是,无论检查仪器多么先进,都离不开医生的知识、经验和判断,离不开医生的问诊。
有一次,我应邀到郑州市某医院会诊。患者是一位20多岁的女性,已经病了四个月了。她在四个月前因为说话不清楚到某医院就诊。经治医生立即给她开了脑部磁共振检查。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提示她左侧脑部额顶叶有一血管瘤。于是医生认为他找到了这位患者说话不清楚的病因,以后的所有医生都按照这个线索为病人进行检查和治疗。
她进行了包括磁共振血管造影(MRA)、CT血管造影(CTA)和DSA等几乎所有现代医学能够进行的影像学检查,证明她确实患有左侧额顶部动静脉畸形。这种动静脉畸形是先天的,可以造成患者癫痫发作和脑部出血,应该进行手术治疗,于是她在某医院做了脑部γ-刀手术,导致了右侧肢体轻度偏瘫。但她的说话不清的症状没有任何减轻,而且有所加重,并出现了吞咽困难。在本次住院后因严重的吞咽困难,终于下了胃管。
这次的经治医生是一位有经验的内科医生。她认为患者脑部的病变不至于产生现在的症状,但不知道患者究竟患的是什么病。于是请求会诊。
吞咽困难是一种常见的症状。80%以上的舌咽困难可根据病史推断出其病因。我的任务是首先将其分为梗阻性和神经肌肉性两大类。我熟悉的是神经肌肉性者。如果是梗阻性的,那只能是另请高明了。
神经肌肉性的吞咽困难是神经系统疾病的常见症状。可见于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如脑血管病、帕金森病、脑干肿瘤、肌萎缩侧索硬化、多发性硬化、Huntington病、脊髓灰质炎和梅毒感染后等),周围神经病和神经-肌肉接头病(重症肌无力)还有肌病(多发性肌炎、皮肌炎等)。
她究竟是什么病?我又一次详细的询问了病史。我很走运。通过问诊,我迅速了解到患者虽然有吞咽困难,但却没有饮水发呛,喝水和进食稠的东西一样困难,可能是吞咽无力,而且患者提到早餐时会好一些。早餐时好一些?中午和晚上重?说话不清也是早晨轻,晚上重?患者均做了肯定的回答。
于是我立即想到这个患者的疾病具有“晨轻暮重”现象,一个可能的诊断立即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她有可能是“重症肌无力”!
我详细为患者进行了神经系统检查:患者神智清楚,检查合作。下着胃管接受检查,说话声音低微,带鼻音。眼球各向活动尚可,无复视,无眼震。额纹及鼻唇沟对称。伸舌无偏歪,舌肌无萎缩。双侧咽反射存在。左侧上下肢肌力正常,右侧上下肢肌力4-5级。右侧上下肢腱反射活跃,巴氏征阳性(脑部γ-刀手术,导致了右侧肢体轻度偏瘫)。感觉及共济运动无异常。
她是真性球麻痹? 不是。因为她没有舌肌萎缩,咽反射存在,也没有引起真性球麻痹的疾病史如延髓梗塞的病史、体征和影像学异常。也没有格林-巴利综合症的可能。
她是假性球麻痹?不是。她只有单侧病理反射,而且是在脑部γ-刀手术之后,显然是γ-刀手术对脑部的创伤所致。
我建议为患者进行新斯的明试验,并做重复神经电刺激试验和胸腺检查。请求会诊的医生为她注射一支新斯的明,10分钟后,她奇迹般地恢复正常了。重复神经电刺激试验,则出现动作电位递减现象,支持重症肌无力的诊断。患者连续几天口服常规剂量的溴吡斯的明后再到门诊见我时,已经恢复到正常状态。她的说话不清和吞咽困难是重症肌无力所致。脑动静脉畸形仅仅是并存的无症状性病灶。
这是重检查,轻病史,不进行分析导致误诊、误治的典型病例。问诊在这一病例的诊断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决不是神经影像新时代三个代表所能代替的!
比如在神经内科门诊非常常见的头晕,就比较难以问清楚。病人描述头昏眼花、几乎晕厥或者是旋转的感觉。此时,医生要弄清楚是外部环境在动还是患者自己在动(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最重要的是,是否有其他伴随症状和体征,如无力、麻木或吞咽困难等。如果症状只是涉及头晕,而无伴随症状和体征,病因极有可能是外周性的。如伴有无力、颅神经受累和感觉障碍,则是脑干问题。
4、正确使用低度和高度操纵模式,避免两个极端
在询问病史时,会产生两个极端情况。一是被动倾听,对患者选择的谈话内容不加任何的提示、影响和干预。二是医生不断发问,甚至按照个人的固有思维去诱导病人。一定要设法避免这两个极端。
可以将医生与病人的谈话分成两种模式,即低度操纵模式和高度操纵模式。低度操纵模式可以称为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谈话,高度操纵模式则是以医生为中心的医患交流。两种模式都很重要并且有用。通常在医患谈话中应包括两种模式的互相转换,交替使用。
在与病人谈话的开始,一般应使用低度操纵方式。问:您是哪里人?哪里不舒服?或者您这次来医院就诊是因为什么?让病人在毫无拘束的情况下谈自己的病情。医生则应该认真倾听。如果我们学会了用自己敏感的耳朵去聆听,就可能在病人的述说中得知他们对疾病的感受,疾病是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或者是他们对可能存在的疾病的担心是什么,以及他们希望从这次就诊中得到什么。
患者可以因为许多原因来就诊:有些时候是某种症状很重需要解决,如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头痛。急性脑梗塞的偏瘫、失语等。有些是因为担心别的医院或医生诊断的不准确(如腔隙性脑梗,脑白质脱髓鞘,脑供血不足等)。有些是因为朋友或邻居有某一症状后来死亡了,现在病人也有类似症状,惶惶不可终日。有些是因为工作或家庭或社会关系上出了问题,导致他们心理上的障碍,而这些障碍却以头晕、头痛、失眠等为主诉来就诊。
敏锐的医生可以从这种低度操纵模式中,从病人谈话的内容、语调、表情等了解到患者就诊的重要原因和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
然后可以过渡到医生高度操控模式。详细地询问症状的各种细节(如头痛的性质、部位、持续时间、诱因、伴随症状、加重和缓解因素。如头晕,时间、起病方式、眩晕、晕厥前、失衡、头重脚轻等)。
这时候,医生要应用自己的医学知识,提出并检验自己的诊断假设。足够的神经系统疾病和神经症状鉴别诊断知识储备是绝对需要的。从首发症状开始,让病人按时间顺序对疾病进行“事件全程浏览”
由于病人和家属缺乏医学知识,尤其是神经病学知识,他们往往不知道如何开始叙述病史。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是:让病人从首发症状开始,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叙述病史。
有人发现一种方法,称其为“事件全程浏览”,对阐明症状的性质和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实际上,这种“事件全程浏览”并不是新的发明,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按时间顺序叙述病史。
我深切体会到,使用这种“事件全程浏览” 或按时间顺序叙述病史的方法确实能正确地反映出病人的真实情况,而且不会有重要遗漏。用这种方法,我常能发现病人病史中的某些重要遗漏而使诊断明朗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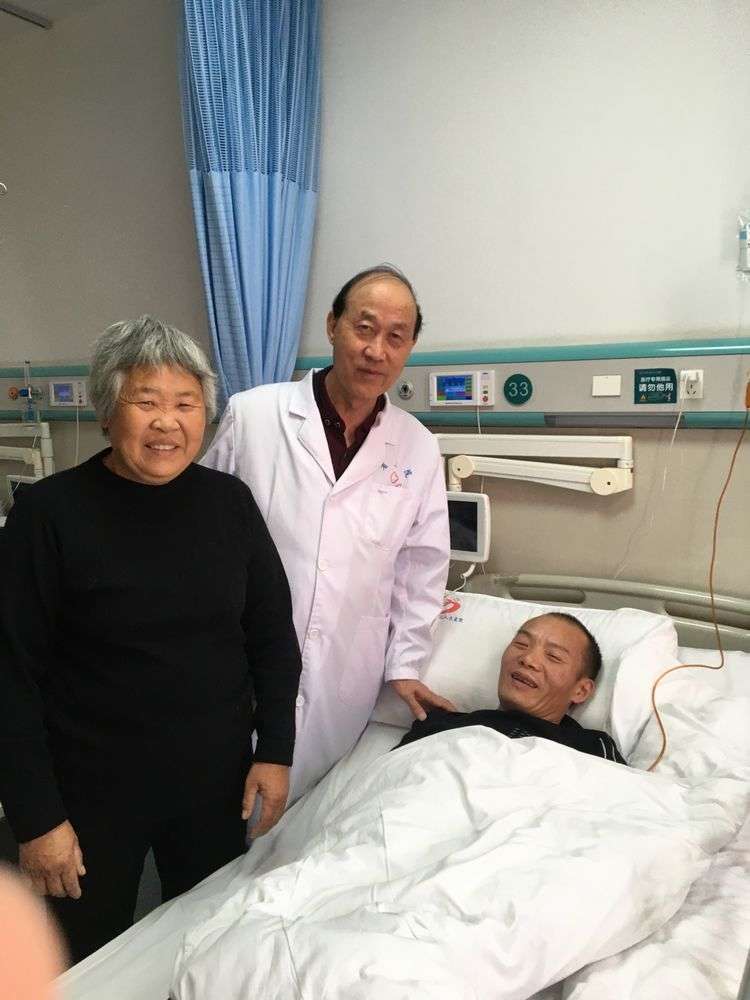

本文是冯周琴版权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本文仅供健康科普使用,不能做为诊断、治疗的依据,请谨慎参阅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