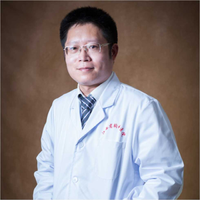 三甲
三甲
往昔今昔:再谈复治肺结核治疗
中国防痨杂志
2021年第4期
·述评·
往昔今昔:再谈复治肺结核治疗
马艳 沈鑫 高微微
复治肺结核与初治肺结核相比,具有治疗时间长、治疗成功率较低及耐药率更高的特点,在肺结核中占有较高比例。通过规律治疗,复治肺结核患者治疗成功率可达80%以上。但在临床诊疗过程中,仍存在部分患者用药不合理、患者治疗依从性差及不规律治疗等情况,导致病情恶化,产生耐药或耐多药,或进展为慢性结核病,成为耐药肺结核传播的重要来源。目前,复治肺结核已成为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的重点与难点,给终止结核病目标的实现带来严峻挑战。
复治肺结核疾病负担高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全球结核病报告显示,2019 年各国登记并报告结核病患者749.5万例,其中,新发及复发结核病患者约710.3万例,复治患者约39.2万例(复发患者除外)。复治登记报告的病例不同国家差异较大,通常在耐多药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中所占比例较高[1]。此外,复治肺结核患者中发生耐药的比例较初治肺结核患者更高。2019年,全球3.3%的新发结核病患者和17.7%的复治患者患耐多药/耐利福平结核病(MDR/RR-TB),复治肺结核患者中耐多药患者比例高达50%。俄罗斯第四次抗结核药物耐药调查报告指出,新发患者及复治患者中耐多药患者的比例分别为13%和48.6%[2]。乌克兰第一次全国调查发现,新发患者和复治患者中耐多药患者的比例分别为19.2%和40.7%[3]。巴基斯坦的一项研究表明,46.9%的复治患者对至少一种抗结核药物耐药,24.3%为耐多药[4]。
2019年,我国登记的病原学阳性患者中复治患者为3.98万例,占11.9%。此外,复治患者中MDR/RR-TB高达23%,高于初治肺结核患者中的比例(7.1%)[1]。1979年、1984—1985年、1990年、2000年我国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显示,复治患者的耐药率依次为61.8%、64.1%、41.1%、46.5%,均高于初治患者。2010 年全国第五次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复治患者对11种一线和二线抗结核药品的任一耐药率为38.5%[5]。马艳等[6]研究表明,复治肺结核患者耐药率为39.3%,既往治疗2次及以上的患者发生耐药的风险是治疗1次的2.166倍,多次反复治疗是复治肺结核患者发生耐药的危险因素。黄曙海等[7]研究表明,接受过2次及以上治疗的肺结核患者总耐药率高。此外,复治本身也是患者发生耐药的危险因素。因此,复治肺结核患者更易发生治疗失败;治疗失败与产生耐药明显相关,复治、耐药及治疗失败相互影响,若不进行规范治疗与管理,将进一步形成恶性循环。
复治肺结核治疗方案的选择应更多关注
1993年,WHO宣布全球处于结核病紧急状态,并提出DOTS策略,其中,提出直接面视下的督导治疗。1997年,WHO提出对于应用Ⅰ类治疗方案(2H-R-E-Z/4H2-R2;H:异烟肼;R:利福平;E:乙胺丁醇;Z:吡嗪酰胺)治疗失败的复治患者进行标准化短程复治方案,即Ⅱ类治疗方案(3S-H-R-E-Z/5H2-R2-E2;S:链霉素)[8]。而Espinal等[9]对于Ⅰ类方案治疗失败再进行Ⅱ类方案治疗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2003年,WHO提出对于复治肺结核患者基于其治疗史,推荐标准化治疗方案(Ⅱ类方案),即:2H-R-Z-S-E/1H-R-Z-E/5H-R-E[10]。此方案的实施,对控制结核病起到了一定成效。然而,随着药物敏感性试验(简称“药敏试验”)的逐步开展,以及耐药结核病的流行,此方案的治疗成功率相对较低,因此,该方案的实施及推广受到了较多的质疑。在摩洛哥进行的一项针对WHO推荐的Ⅱ类治疗方案疗效的比较研究中,应用Ⅰ类治疗方案治疗失败和治疗不满1个疗程即中断治疗的患者中,应用Ⅱ类治疗方案的复治肺结核患者的治疗成功率分别为58.0%和51.4%[11]。来自乌干达的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表明,使用Ⅰ类治疗方案的治疗成功率为46%[12]。2006—2009年在格鲁吉亚开展的应用Ⅱ类治疗方案治疗复治肺结核的研究显示,治疗成功率为52%~64%,总治疗成功率为58%(3858/6683)[13]。此外,在土耳其开展的研究表明,应用Ⅱ类治疗方案治疗初治失败及不规则治疗肺结核患者的治愈率分别为52.2%和38.4%[14]。Ⅱ类治疗方案对复治肺结核患者治疗效果不理想,与复治患者中耐药比例较高有关。来自伊朗的研究表明,应用Ⅰ类治疗方案治疗失败或存在不规则治疗史的患者,其耐多药发生率分别为56%和55%[15]。因此,一些有能力开展药敏试验的国家开始对复治方案进行调整。Tabarsi等[15]对基于药敏试验的再治疗策略和用修订的Ⅱ类治疗方案中间方案替代Ⅱ类治疗方案可能改善Ⅰ类方案治疗失败和未确诊的活动性、传染性MDR-TB患者的临床效果。这一战略大大降低了MDR-TB诊断和治疗延误的比例。修订后的方案治疗MDR-TB和Ⅰ类治疗方案治疗失败和不规则治疗患者的成功率分别达到了62.2%和72%。在巴西,修订后的复治方案应用于治疗依从性好的患者的治愈率可达88%[16]。
我国的标准化复治方案为2H-R-E-Z-S/6H-R-E,即强化期2个月使用异烟肼、利福平、乙胺丁醇、吡嗪酰胺和链霉素五联治疗,继以6个月的异烟肼、利福平、乙胺丁醇三联巩固期治疗;或3H-R-E-Z-S/6H-R-E,2H3-R3-Z3-E3-S3/6H3-R3-E3[17]。该方案的治愈率曾达到90%以上[18]。随着药敏试验的普及,耐药结核病疫情的上升及我国结核分枝杆菌耐药形式的转变,我国学者近年对该方案进行了再评价,认为此方案治疗复治肺结核已不尽合理[19-20]。戈启萍等[21]对国内多中心的复治肺结核患者使用标准化复治化疗方案治疗后发现,药物敏感的复治肺结核患者与多耐药复治肺结核患者,其治愈率分别为94.3%和70.2%。范玉美等[22]研究发现,复治肺结核患者应用标准化化疗方案的治疗成功率及治愈率分别为74.9%和56.5%;吴哲渊等[23]研究发现,复治肺结核患者应用标准化化疗方案的治疗成功率为47.5%。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复治肺结核的治疗新方案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沙巍等[24]对全国17家结核病防治机构的首次复治涂阳肺结核患者(542例)进行治疗研究,各组患者结束治疗后随访2年,比较新方案的疗效、依从性、不良反应发生率和复发率。结果表明,包含对氨基水杨酸异烟肼(Pa)、利福布汀(Rfb)、乙胺丁醇、吡嗪酰胺、莫西沙星(Mfx)的短程化疗方案治疗首次复治肺结核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优于标准复治方案。梁爽等[25]应用抗结核固定剂量复合制剂联合左氧氟沙星治疗复治涂阳肺结核患者取得了较好的疗效。Zhang等[26]开展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研究显示,与标准化方案相比,中医药联合标准化方案治疗促进了复治肺结核患者病灶的吸收和痰菌阴转率。杜建等[27]开展了一项不同化疗方案对复治肺结核患者治疗效果的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结果表明优化后的复治肺结核的治疗方案即高剂量方案和长疗程方案的治疗成功率分别为84.9%和73.5%,均高于标准化治疗方案62.2%的治疗成功率。
复治肺结核合理有效的治疗新方案亟待探索
由于复治肺结核患者有较高的耐药比例,因此,制定合理有效的方案,降低治疗失败率,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难题。WHO在2017年提出不再规定Ⅱ类方案(标准化方案),指导方针主张逐步取消Ⅱ类方案,应根据药敏试验结果选择治疗方案。此外,《中国结核病预防控制工作技术规范》(2020年版)也指出活动性肺结核患者根据肺结核病情和耐药情况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分为利福平敏感肺结核(采用利福平敏感治疗药物和方案)和利福平耐药肺结核(采用利福平耐药治疗药物和方案)。然而,对于没有能力开展药敏试验的国家和地区,复治肺结核治疗方案应如何制定,则需要更多的探索。从治疗患者和控制传播的角度讲,在治疗过程中应注意复治肺结核患者的复治类型,需根据其不同的特征选择合理的治疗方案,同时应继续深入开展研究复治类型与治疗效果的关系。
尽管WHO和我国所推荐的标准化复治肺结核化疗方案都曾经是一种经济、高效的方案,也是治疗复治肺结核患者的重要手段。但我国结核病防治策略在变化,社会和经济在发展,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也在调整,加之耐药态势高居不下,因此,长期推行单一、无选择的标准复治化疗方案已不适应当前防治策略。尽管我国指南推荐的标准化方案仍然是大多数肺结核患者的首选,但同时也应考虑患者自身特点选择合理的方案,如应尽可能进行药敏试验,选择含4种以上敏感药物组成的新方案;未获药敏试验前或无药敏试验条件,需根据用药史选择可能的敏感药物组成新方案;必要时可对免疫力低下患者加用免疫调节剂或中药辅助治疗,改善细胞免疫功能,增强化疗疗效,使部分患者痰菌阴转,病灶吸收好转;接受规范抗结核治疗无效而反复排菌的患者应进行非结核分枝杆菌菌种鉴定、奴卡菌病鉴别、耐药和抗结核药物的血药浓度等检查,勿随意归为复治肺结核或MDR-TB。在复治肺结核治疗过程中,对患者痰标本细菌学检查的监测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治疗的前2个月,即强化治疗期间,应该每月常规对患者进行痰标本细菌学检查。对于细菌学检查仍为阳性的患者,应及时进行药敏试验,根据试验结果及时调整化疗方案。此外,还应加强对患者的管理,积极开展患者及其家属的健康宣教,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早期发现并发症并及时处理,以进一步降低治疗失败的风险。未来,应进一步加大经费投入,开展有一定规模的前瞻性的复治化疗新方案研究。
参 考 文 献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lobal tuberculosis report 2020.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
[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ti-tuberculosis: drug resistance in the World(Report No 4).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8.
[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 Tuberculosis surveillance and monitoring in Europe 2015. Stockholm: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 2015.
[4] Javaid A, Hasan R, Zafar A, et al. Pattern of first- and second-line drug resistance among pulmonary tuberculosis retreatment cases in Pakistan. Int J Tuberc Lung Dis, 2017, 21(3): 303-308. doi:10.5588/ijtld.16.0444.
[5] 全国第五次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技术指导组, 全国第五次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办公室. 2010 年全国第五次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报告. 中国防痨杂志, 2012, 34(8): 485-508.
[6] 马艳, 杜建, 高微微, 等. 377例复治肺结核患者耐药的危险因素研究.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 2018, 19(9): 641-646. doi:10.16506/j.1009-6639.2018.09.001.
[7] 黄曙海, 蓝如束, 刘飞鹰, 等. 广西壮族自治区肺结核耐药性调查及复治患者耐药相关因素分析. 中国防痨杂志, 2013, 35(9): 711-717.
[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reatment of Tuberculosis: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TB programme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97.
[9] Espinal MA, Kim SJ, Suarez PG, et al. Standard short-course chemotherapy for drug-resistant tuberculosis: treatment outcomes in 6 countries. JAMA, 2000, 283(19): 2537-2545. doi:10.1001/jama.283.19.2537.
[10]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reatment of tuberculosis. 3rd ed.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3.
[11] Ottmani SE, Zignol M, Bencheikh N, et al. Results of cohort analysis by category of tuberculosis retreatment cases in Morocco from 1996 to 2003. Int J Tuberc Lung Dis, 2006, 10(12): 1367-1372.
[12] Nakanwagi-Mukwaya A, Reid AJ, Fujiwara PI, et al. Characteristics and treatment outcomes of tuberculosis retreatment cases in three regional hospitals, Uganda. Public Health Action, 2013, 3(2):149-155. doi:10.5588/pha.12.0105.
[13] Furin J, Gegia M, Mitnick C, et al. Eliminating the category Ⅱ retreatment regimen from national tuberculosis programme guidelines: the Georgian experience. Bull World Health Organ, 2012, 90(1): 63-66. doi:10.2471/BLT.11.092320.
[14] Saka D, Aydowidth=5,height=9,dpi=110du M, Caliwidth=4,height=7,dpi=110ir HC, et al. The treatment results of retreatment pulmonary tuberculosis patients in our clinic. Tuberk Toraks, 2011, 59(2): 111-119. doi:10.5578/tt.1932.
[15] Tabarsi P, Chitsaz E, Tabatabaei V, et al. Revised Category Ⅱ regimen as an alternative strategy for retreatment of Category Ⅰ regimen failure and irregular treatment cases. Am J Ther, 2011, 18(5): 343-349. doi:10.1097/MJT.0b013e3181dd60ec.
[16] Pedro PD, Rizzon CF, Bassanesi SL, et al. Retreatment of tuberculosis patients in the city of Porto Alegre, Brazil: outcomes. J Bras Pneumol, 2011, 37(4):504-511. doi:10.1590/s1806-37132011000400013.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政司,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结核病防治规划实施工作指南. 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9: 52-70.
[18] 符彩云, 符致顺. 1500例复治涂阳肺结核成因及疗效分析. 中国防痨杂志, 2000, 22(2): 91-92.
[19] 高微微.对复治肺结核患者的规范化治疗和个体化治疗的一点看法.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04, 27(2): 81-83.
[20] 杨国儒, 张绍坤, 王国锋, 等.对复治肺结核患者的规范化治疗和个体化治疗的几点思考.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04, 27(2): 78-79.
[21] 戈启萍, 杜建, 姜广路, 等.标准复治化疗方案治疗多耐药与敏感复治肺结核患者的对比研究. 中国防痨杂志,2015,37(8): 879-884. doi:10.3969/j.issn.1000-6621.2015.08.017.
[22] 范玉美, 肖和平, 梅建. 首次复治肺结核患者疗效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 2007, 7(3): 159-163.
[23] 吴哲渊, 张青, 张祖荣, 等. 上海市耐多药肺结核防治管理模式效果评价.中国防痨杂志, 2015,37(11): 1118-1125. doi:10.3969/j.issn.1000-6621.2015.11.008.
[24] 沙巍, 张青, 崔文玉, 等. 首次复治肺结核患者短程化疗新方案的临床研究. 中国防痨杂志, 2017, 39(1): 39-45. doi:10.3969/j.issn.1000-6621.2017.01.011.
[25] 梁爽, 韩东伟, 钟威, 等. 抗结核固定剂量复合制剂联合左氧氟沙星治疗复治涂阳肺结核患者的效果分析. 结核病与肺部健康杂志, 2019, 8(2): 149-152. doi:10.3969/j.issn.2095-3755.2019.02.016.
[26] Zhang SY, Fu JY, Guo XY, et al. Improvement cues of lesion absorption using the adjuvant therap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Qinbudan tablet for retreatment pulmonary tuberculosis with standard anti-tuberculosis regimen. Infect Dis Poverty, 2020, 9(1): 50. doi:10.1186/s40249-020-00660-z.
[27] 杜建,刘宇红,李亮,等.复治肺结核患者采用不同化疗方案的效果评价.中国防痨杂志,2016,38(10):850-857. doi:10.3969/j.issn.1000-6621.2016.10.013.
width=69,height=69,dpi=110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的开放科学计划以二维码为入口,提供丰富的线上扩展功能,包括作者对论文背景的语音介绍、该研究的附加说明、与读者的交互问答、拓展学术圈等。读者“扫一扫”此二维码即可获得上述增值服务。
doi:10.3969/j.issn.1000-6621.2021.04.002
基金项目:“十三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8ZX10722302-003);“十二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3ZX10003009-001-006、2013ZX10003009-001-007、2013ZX10003009-001-008、2013ZX10003009-001-009);“十一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08ZX10003-015-2)
作者单位:100700 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基础所(马艳);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与艾滋病防治所(沈鑫);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治临床中心(高微微)
通信作者:高微微,Email: gwwjys@sina.com;沈鑫,Email: shenxin@scdc.sh.cn
(收稿日期:2021-03-10)
(本文编辑:李敬文)
本文为转载文章,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本文仅供健康科普使用,不能做为诊断、治疗的依据,请谨慎参阅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