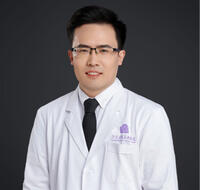
获得性慢性假性肠梗阻的极其罕见病因——“自身免疫性肠平滑肌炎“附3例长期随访病例报道
大多数引起慢性假性肠梗阻的肠道自身免疫性疾病是自身免疫性肠神经节炎,此类患者外周血肠神经抗体升高[1]。但自身免疫性肠平滑肌炎是肠壁固有肌层受到大量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攻击所致,伴或不伴外周血肠平滑肌抗体升高,是获得性慢性假性肠梗阻的极其罕见的病因,多见于儿童。截止2005年为止,文献共报道11例,包括5例成人、1例儿童、5例婴幼儿[1,2-6]。自2005年-2022年的17年间,未再有此类患者报道。
1.临床表现
该病一般于出生后6个月到2.5年首次发病。首次发病前正常生长。这些患者的临床经过基本表现为,无明显诱因的急性腹泻,继之以顽固性、难以缓解的肠梗阻。病人主要表现为腹胀、腹痛,肠管严重扩张。经口进食不能,肠内营养严重不耐受。此类患儿一般都是足月产。可以同时合并自身免疫性肝炎等。文献报道,自身免疫性肝炎表现为肝脏出现进行性纤维化[1]。
2.病理表现
病变主要累及肠壁固有肌层[1],肠壁固有肌层被大量CD3+、CD8+淋巴细胞弥漫性、透壁性浸润,以CD8+淋巴细胞为主,偶见CD20+ B淋巴细胞。部分患者固有肌层还约有20%淋巴细胞表达穿孔素和颗粒酶B。粘膜及粘膜下层不受累或仅少量炎症细胞侵染,表现为慢性炎症改变。不伴神经细胞损害,黏膜下和肌间神经丛完整。
大量的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浸润于肠壁固有肌层多见于该病的早期。随诊疾病的进展,逐步出现严重的平滑肌变性、丢失,代之以严重纤维化、肠壁增厚。严重者,甚至出现肠壁神经节变性。且患者每次发作,即便治疗有效,仍会有一部分肠壁平滑肌丢失,肠壁纤维化,肠功能进一步受到损害。
研究发现,上述病变只累及十二指肠、小肠、结肠,且以十二指肠、小肠为主,不累及食管、胃、直肠和其他富含平滑肌的空腔脏器。
3.发病机理
目前尚不清楚大量淋巴细胞浸润肠壁固有肌层导致肠道平滑肌炎的具体发病机制。但可以确定的是,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在该病的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7-8]。
4.诊断
除了临床表现外,病变肠壁病理是确定诊断的金标准。但由于病变主要累及肠壁固有肌层,黏膜及粘膜下层不受累或轻度炎症细胞浸润。所以,自身免疫性肠平滑肌炎的确诊必须依靠肠壁全层病理而不是粘膜病理。由于该病的罕见性及临床医师的对于该病陌生,患者往往被诊断为慢性炎症,贻误病情。
另外,大部分患者外周血可检出自身抗体: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ANCA)、抗核抗体、抗DNA抗体、抗平滑肌抗体。但也可阴性。抗体仅可作为参考。
5.鉴别诊断
自身免疫性肠平滑肌炎主要与自身免疫性肠病鉴别诊断。两者名称相似,实则病理表现及临床症状差异颇大。自身免疫性肠病的临床表现以顽固性腹泻、重度营养不良为主,无肠梗阻症状。诊断条件为[10]:
1) 慢性腹泻达6周以上,不存在肠梗阻表现;
2) 吸收不良,出现严重体重下降;
3) 小肠绒毛部分或全部萎缩、变钝,深部隐窝淋巴细胞增多,隐窝内凋亡小体形成和淋巴细胞浸润,表面上皮内淋巴细胞增多不明显;杯状细胞或潘氏细胞减少或消失。病情较重的患者,可能出现隐窝脓肿。
4) 除外其他原因导致的绒毛萎缩;
5) 有些患者血清中存在肠上皮细胞抗体、抗杯状细胞抗体等。
其中,1)-4)为诊断必备条件,5)为非必需条件。免疫抑制治疗有效。
6.治疗
1).免疫抑制治疗
所有的患者均对激素首次治疗有效,只有极少数患者出现完全缓解[5]。免疫抑制治疗有依赖性,大多数患者随着激素减停而出现复发[4]。随着疾病进展,同等剂量的激素难以奏效,需要加大剂量或加用其他类型免疫抑制药,如骁悉、环孢素、他克莫司等[9]。
另外,临床发现,每次激素治疗有效后,即便再次耐受肠内营养,但耐受性明显降低,需要肠外营养作为补充性营养支持治疗[1]。实际上,病理也仍在进展,主要表现为虽然淋巴细胞明显减少,但肠壁肌肉坏死、变性,肠壁健康肌肉细胞逐步丢失、代之以纤维化。即进行免疫抑制治疗后,肠壁肌肉细胞仍会进行性纤维化,肠功能损害进一步加重。肠壁纤维化的后果就是患者对激素治疗的抵抗。
目前,非手术治疗中,只有免疫抑制治疗有效。如果早期免疫抑制治疗积极的话,可防止出现肠功能衰竭。但该病的罕见性及临床医师的对于该病不熟悉,导致最终确诊时多数患者处于肠功能衰竭状态,早已失去最佳治疗时机。
2).小肠移植手术
小肠移植是此类患者的最后治疗手段。由于患者十二指肠、小肠受累较为严重,单独小肠移植并不能从根本解决肠功能衰竭,一般行改良腹腔器官簇移植手术,将患者病变消化道切除,移植器官包括胃、十二指肠、胰腺、小肠。但移植手术虽然将病变消化道完全切除,代之以健康的肠道,但并没有根治原发病,移植术后,患者自身免疫系统仍会攻击移植小肠,出现同样的病理表现。因此,在小肠移植术后,在抗排异治疗的同时,还应时刻监测原发病的活动情况,警惕原发病复发。
总结
自身免疫性肠平滑肌炎是获得性慢性假性肠梗阻极其罕见的病因,多见于儿童患者。受累肠道固有肌层高密度淋巴细胞浸润、平滑肌纤维降解并被纤维组织替代是其组织病理学特点。该病的确诊需要扩张肠管的全层病理。临床上如果遇到反复发作、迁延不愈且多次手术证实无机械性梗阻的肠梗阻患者,应该想到自身免疫性肠平滑肌炎继发慢性假性肠梗阻的可能。免疫抑制治疗虽然能使病情短暂缓解,但并不能改变疾病发展进程,肠功能衰竭不可避免。小肠移植是使病人获得良好预后的根本性治疗办法,但术后要警惕原发病复发。
病例1[4].
患儿足月产,出生体重3.2kg,母乳喂养,生长未见任何异常。2岁时,患儿无明显诱因出现急性急性腹泻。腹泻缓解后,出现严重的肠梗阻,且无法经口进食,不能耐受肠内营养,依靠全肠外营养支持。肠梗阻呈持续、进行性加重趋势。影像学检查未发现肠道机械性梗阻。发病1个月后,患者进行第1次腹腔镜探查,肠管严重扩张,未见机械性梗阻。血化验提示,血常规、肝肾功能正常,红细胞沉降率、C反应蛋白明显升高。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ANCA,1:2000)、抗核抗体(1:80)、抗DNA抗体(1:150)、抗平滑肌抗体阳性(1:500)。体表胃电图显示,胃窦及十二指肠均无主频存在(即胃电活动无规律,正常胃电是每分钟3周主频)。由于患者肠梗阻症状不缓解,也为了明确病理诊断,进行第2次腹腔镜探查,获取回肠及结肠的肠壁全层病理。病理显示,回肠和结肠的整个固有肌层炎症较重,肠梗阻的症状恐与肠壁炎症有关。
治疗方面包括:1)患者严格禁食水,全肠外营养支持;2)鼻-胃管减压;3)环丙沙星和青霉素可预防小肠细菌过度增殖;4)西沙必利(0.2 mg/kg,TID)和异氯匹胺(0.5 mg/kg,TID)肠动力,但效果不佳。5)免疫抑制治疗:强的松20mg/kg/d。免疫抑制治疗后,患者肠动力改善,肠梗阻症状逐步缓解,重新耐受肠内营养。免疫抑制1个月后,强的松减至0.5mg/kg/d,持续1周后,停药。停药后再次出现腹胀、呕吐。恢复免疫抑制治疗后,肠梗阻症状再次缓解。后续的9个月中,肠梗阻平均每月发作1次,都与激素剂量减停或感染有关。
强的松治疗1年后,肠梗阻再次严重发作。提高强的松剂量至2mg/kg/d,仍不能缓解肠梗阻症状。遂进行第3次腹腔镜探查发现,腹腔粘连广泛,并再次获取肠道全层病理。血化验仍提示,ANCA(1:4000)、抗平滑肌抗体阳性(1:500)。改善肠动力方面,在西沙必利和异氯匹胺基础上,加用红霉素1mg/kg,QID,但收效甚微。鉴于外周血循环抗体升高,在强的松基础上,加用硫唑嘌呤(2mg/kg/d)和环磷酰胺(2mg/kg/d)。重新调整免疫抑制治疗后,肠梗阻症状稍有改善。加用环孢素,每次5mg/kg,BID,血浆环孢素目标浓度120-150mg/L。
强的松联合环孢素方案实施后,患者肠梗阻快速缓解,ANCA浓度快速下降并消失。患者很快开始耐受肠内营养。在后续的2年中,肠梗阻间断发作,均与肠道细菌过度增殖有关。后来,患者又出现了一次严重的肠梗阻发作伴出血性胃炎。患者再次恢复全肠外营养支持。此时,患者进行了第4次腹部手术,获取肠管全层病理发现,肠壁固有肌层炎症细胞明显减少,但肠壁平滑肌细胞却大量丢失。血肌酐却明显上升,考虑与患者接受2年的环孢素治疗导致肾功能损害有关,肾穿刺病理(肾小管上皮空泡化)也证实了这一点。将环孢素血液浓度降至50mg/L后,血肌酐恢复正常水平。
截止发稿时,患者不能经口进食,不能耐受肠内营养,仍使用全肠外营养支持。免疫抑制方案为静脉强的松,17.5mg/d;环孢素,10mg/d;腹胀严重,造口持续脱垂。
病例2[1].
患儿女性,足月产。出生18个月时出现肝功能损害。自身免疫指标显示,平滑肌抗体(SMA,1:40)和血清免疫球蛋白IgG增加。抗核抗体(ANA)、抗线粒体抗体(AMA)、ANCA和肝肾微粒体抗体检测均为阴性。肝穿刺组织学检查发现,严重活动性肝炎并伴有肝组织纤维化。泼尼松和硫唑嘌呤治疗后,转移酶水平恢复正常。2年后的第2次活检显示,持续性肝炎伴T淋巴细胞浸润,以及皮质类固醇治疗引起的肝细胞广泛脂肪变。同时门静脉纤维化改变。
5岁时,患者出现了无明显诱因的急性腹泻,腹泻缓解后出现难以缓解的肠梗阻。当时使用药物包括强的松(0.3和0.5mg/kg交替)和硫唑嘌呤(3mg/kg)。腹部X片显示,小肠明显扩张,尤其是空肠扩张尤为严重。消化道造影可见,造影剂移动缓慢。腹腔镜探查发现,除少许粘连外,肠道无机械性梗阻。
免疫方面检查发现,抗平滑肌抗体1:160,ANA、ANCA、AMA和肝肾微粒体抗体仍为阴性。针对胃壁细胞、网状纤维和肠壁神经的抗体也呈阴性。淋巴细胞计数为4000/ul个。CD4/CD8比值降至0.63。外周血B淋巴细胞(CD3/CD19+)和自然杀伤细胞(CD16+/CD56+)分别下降至2%和3%。血清IgG和C-反应蛋白水平分别升高至34g/L和35mg/L。红细胞沉降率为22mm/h。
胃肠镜获取胃、十二指肠、回肠、结肠、直肠粘膜病理显示,胃、十二指肠粘膜表现为轻度慢性炎症。幽门螺旋杆菌阴性。未观察到十二指肠粘膜绒毛萎缩或上皮间淋巴细胞增多。回肠粘膜也出现上述表现。而结直肠粘膜隐窝结构正常,淋巴细胞轻度浸润,无慢性炎症改变。
由于消化道粘膜病理并未提供与肠动力障碍有关的信息,遂进行第1次腹腔镜手术,目的是获取空肠、回肠、结肠全层病理。病理显示,空肠和回肠粘膜显示绒毛变钝,粘膜间质和粘膜肌层有中度T淋巴细胞浸润,粘膜肌层完整。然而,固有肌层显示,平滑肌纤维减少和退化,且被高密度的CD3+/8+ T淋巴细胞浸润,少量CD20+的淋巴细胞浸润。约20%的淋巴细胞表达穿孔素和颗粒酶B。CD56N-CAM染色显示,肌间神经丛和粘膜下神经丛的神经节完整,无自然杀伤细胞浸润。
基于肠壁全层病理结果,该患者确诊为“自身免疫性肠平滑肌炎症”。患者发病之初,肠动力差,禁食水,依靠全肠外营养支持。免疫抑制治疗(强的松2mg/kg/d和他克莫司)明显改善肠动力障碍。患者再次耐受肠内营养。后续随访17个月,患者肠梗阻症状发作了2次,均发生在强的松减量后。目前,患者仍使用免疫抑制治疗。
病例3.
患者男性,29岁。23岁时无明显诱因出现急性腹泻,对症治疗好转后出现反复发作,迁延不愈的肠梗阻,肠管扩张严重。发病3年后行第1次剖腹探查,小肠明显扩张,未见机械性梗阻。因肠梗阻持续不缓解,5年后行第2次剖腹探查,所见同第一次手术,行回肠、结肠粘膜送病理检查+末端回肠双腔造瘘。回肠、升结肠、乙状结肠、直肠病理提均提示,小块固有肌层及少许粘膜下层,可见肌间神经丛及神经节细胞,肌间见少许慢性炎细胞浸润。ANCA、ANA、抗DNA抗体、SMA均阴性。造口量大,水样。生长抑素、易蒙停控制不佳,经口少量饮水或药物加大造口排量。
患者肠梗阻逐步加重,不能经口进食,肠内营养不耐受,造口量6000-8000ml/d。发病6年后,肠功能完全衰竭,严重水电解质紊乱,极度消瘦(BMI:15.2kg/m2),全肠外营养支持。诊断原发性“慢性假性肠梗阻”,神经病变型可能性大。
发病第7年,患者接受小肠移植——改良腹腔器官簇移植手术,移植器官包括胃、十二指肠、胰腺、小肠。术后病理提示,结肠粘膜慢性炎,局部肌层散在及灶性淋巴细胞浸润,呈肌炎改变。小肠、十二指肠残端小肠粘膜组织慢性炎,局部粘膜上皮糜烂,固有层大量淋巴组织增生,淋巴滤泡形成,局部粘膜肌散乱消失,肠壁环行肌和纵行肌层内多量CO3+和CD8+的T淋巴细胞浸润,病变最重处浆膜下间隙及肌层带状淋巴细胞浸润,肌纤维变性,减少,平滑肌胞浆内见色素颗粒,MASSON染色示平滑肌组织内纤维组织增生,肌间神经节、粘膜下神经节及Cajal细胞未见减少及异常,浆膜层纤维组织增生,伴局部纤维素渗出。诊断为“自身免疫性肠平滑肌炎”、获得性“慢性假性肠梗阻”。术后在抗排异治疗的同时,定期观察原发病活动迹象。术后随访7个月时,患者一般情况良好,正常饮食,营养状况恢复正常,原发病无复发迹象,已经恢复正常生活。
经检索文献发现,该患者是目前世界上首例确诊“自身免疫性肠平滑肌炎”继发“慢性假性肠梗阻”并接受小肠移植——改良腹腔器官簇移植手术,术后存活良好的患者。
参考文献:
1. Haas Susanne,Bindl Lutz,Fischer Hans-Peter,Autoimmune enteric leiomyositis: a rare cause of chronic intestinal pseudo-obstruction with specific morphological features.[J] .Hum Pathol, 2005, 36: 576-80.
2. Smith VV, Milla PJ. Histological phenotypes of enteric smooth muscle disease causing functional intestinal obstruction in childhood. Histopathology 1997;31:112-22.
3. McDonald GB, Schuffler MD, Kadin ME, Tytgat GN. Intestinal pseudo-obstruction caused by diffuse lymphoid infiltration of the small intestine. Gastroenterology 1985;89:882-9.
4. Ruuska TH, Karikoski R, Smith VV, Milla PJ. Acquired myopathic intestinal pseudo-obstruction may be due to autoimmune enteric leiomyositis. Gastroenterology 2002;122:1133-9.
5. Ginie`s JL, Francois H, Joseph MG, Champion G, Coupris L, Limal JM. A curable cause of chronic idiopathic intestinal pseudo-obstruction in children: idiopathic myositis of the small intestine. J Pediatr Gastroenterol Nutr 1996;23:426-9.
6. Nezelof C, Vivien E, Bigel P, Nihoul-Fekete C, Arnoud-Battandier F, Bresson JL, et al. Idiopathic myositis of the small intestine: a rare cause of chronic intestinal pseudo-obstruction in children. Arch Fr Pediatr 1985;42:823-8.
7. Vergani D, Choudhuri K, Bogdanos DP, Mieli-Vergani G. Pathogenesis of autoimmune hepatitis. Clin Liver Dis 2002;6: 439-49.
8. Gregorio GV, Portmann B, Reid F, et al. Autoimmune hepatitis in childhood: a 20 year experience. Hepatology 1997;25:541-7.
9. Heneyke S, Smith VV, Spitz L, Milla PJ. Chronic intestinal pseudo- obstruction: treatment and longterm follow up of 44 patients. Arch Dis Child 1999;81:21-7.
Freeman HJ.Adult autoimmune enteropathy[J]. World J Gastroenterol,2008
本文是朱长真版权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本文仅供健康科普使用,不能做为诊断、治疗的依据,请谨慎参阅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