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甲
三甲
镜语记:4岁近视1350度
假日复习病历,我翻到一位有髓神经纤维、高度近视、弱视综合征患儿,她2002年初诊时只有3岁。她的右眼视力很差,仅为0.05,度数超过1000度,视力无法提高。孩子的父亲很年轻,每次随访必定陪来,他说,只要孩子视力好,他什么都愿意的。我自己去验光,给出眼镜处方,试配RGP。他说到孩子不太配合训练,他几乎要流泪,我尽可能给予安慰。我给她做过手术,减轻双眼之间的度数落差,后来提升到0.3。我曾与其父亲联系复诊,他说女儿早不太肯听他,听得出他的中年叹息。我又联系他,好像再无回音。
我的小患者中不只是高度近视,也有高度远视,包括先天性白内障术后或合并其他眼病。有位先白宝宝,在罗老师那里手术非常成功,因瞳孔实在太小,我也自己去复光,我确认远视1500度镜方。孩子的母亲非常配合医嘱,积极指导孩子训练,“那不是孩子在做视力训练”,她说“那就像我自己也在做”。孩子做二期人工晶体植入后继续随访,到上学前双眼视力改善到1.0。我以前偶把远期验光报告拍照传给罗老师,为医生手术点赞,为孩子训练加油,为视力康复开心。
高考后总是非常忙,有一天近视手术检查区特别拥挤,我问了一下,竟然有近四百位。一位高中生坐下来时我觉得有些面善,我打开裂隙灯显微镜检查眼睛,其母亲在边上说,他学习成绩很不错,九月要升高三,想假期做激光手术,利于择校和选专业。我提醒她不必着急,激光年龄通常为18岁到60岁,或到年底寒假时再做更好。
那位母亲说,周医生你说过18岁就可以做的,十五年来差不多每年都带孩子来沪看眼睛,他已经满18岁啦!已等十多年,还是早点做吧。她把塞在包里的一叠旧病例取出来。现在医院使用电子病历,患者不必每次出示病例,不过我还是翻开老病历,我看到熟悉的验光单。确实,他在四岁时就来诊,有一眼当时是1350度近视,就是我接诊的。
我看了看孩子母亲,我想起来了,她是一位坚强朴实的母亲。但凡孩子三四岁就近视的,特别是高度近视,做父母的哪会不担心呢?有些父母看到高度近视验光报告就“欲哭无泪”、“忧心忡忡”、“焦虑万分”,有时互相怪罪对方没管好孩子,或没有给孩子健康基因。有些孩子的家长四处寻找“特效“现效”“新法”,恨不得立刻找到立竿见影的方案。他们满心期待找到防治捷径,常常有相似的表述:医生,我不在乎钱,只要孩子视力好!这位母亲早年来时,也是那样状态。
她第一次来时,也想着为了孩子无论如何要试一下“好”方法“新方法”,她说花多少钱都愿意。但当她认认真真追问,迫切地想得到我的确认时,我却严肃地说不用尝试那些听起来有吸引力的“新颖方法”。我对她说,对于大多数近视儿童和青少年,防治需要适宜技术,家长要理性,也要与医生有效沟通。一些家长虽然“不在乎钱”,但医生必须实事求是,重视高质量循证依据。近视防、控、治相关的器械、设施、药物、镜片等,确实不在少数,但绝大多数尚需验证,尚有待科学观察。医生把安全性和有效性放在首位,开出的每一张处方,施予的每一项技术,都要坚持患者至上的原则。出于对五官科医院的信赖,她试着说服自己先随访看看。每一年孩子的度数增加得不多,眼底一直是好的,她因此焦虑消减,渐渐把那些情绪打包放在心底。
这三年因疫情没有来,孩子已窜高很多,怪不得我一下子没认出。我让助手进行全面眼生物参数检查,二个多小时后所有报告都出来,符合手术指证。我综合考虑,这几年他没有定期复查,若再看半年近视稳定性,延到明年初做,会有更好预测性;再则,他是为将来升学做准备而不是当季验兵体测,不需要那么急。我于是对他的母亲说,还是再等一等。他的母亲接受我的建议,安安心心回去。
有一位高度近视女孩的父亲也很信赖我,他的女儿第一次来沪诊疗时刚刚18岁,但已在某个外地医院做晶体手术四年(不是ICL)。从病史上看,孩子六七岁时已有1800度近视,但父母是正常的,我要求他们做唾液基因测试,但没有发现突变。她的角膜内皮数量已很低,低到不得不把人工晶体取出的程度,我于是与他们沟通手术事宜。她的父亲说,就是因为内皮数量减少,当地说要取出晶体,他们才来找我的。我注意到她的自身晶体有片簇状混浊,那混浊形态不那么像人工晶体引起的。我追问病史,手术之前有无自身晶体混浊?家长说应该没有。
屈光晶体取出很顺利,在随后的长期随访中,她的内皮数量稳定,晶体混浊(白内障)没有进展,我每次都要检查周边视网膜,避免视网膜裂孔甚至视网膜脱离的风险。她后来上大学,她毕业、工作、结婚,都是她父亲陪她来看病时告诉我的,他们生活得很好。但我总觉得她是遗传病,一直有疑惑,认为她不是一个普通的高度近视。她结婚后,她的父亲问我,将来孩子会高度近视吗?我说会的,有这个风险,虽然没有检测出基因突变位点。
她正好这三年没有来,她的老父亲陪着她的宝宝来了。他的外祖父与我打招呼,说孩子的妈妈,因为刚刚有了第二个宝宝,不能来复诊。这位4岁宝宝为近视1100度,他很安静地把下巴放到显微镜颏托上,大大的眼睛一眨也不眨。通过散大的瞳孔,我看到孩子有晶体混浊,我立刻想到他的母亲,他母亲也有很相似的晶体混浊形状!显然孩子是先天性白内障,也即,孩子的妈妈也是先天性白内障,而肯定不是当时屈光性晶体手术导致的。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她是遗传病,九年了,没想到通过她孩子的眼部病症而找到证据,那么究竟是哪一种呢?
大约二周后,学生告诉我,血样本基因检测提示COL11A1基因突变,是新的位点,该基因突变可累及全身软骨组织及眼部,符合Stickler 综合征 2型。我反思该例诊疗,虽然没有影响治疗,但由于第一次基因测试未果,加上患者的屈光晶体手术史,让我曾偏向为晶体混浊是手术并发症(基于默认术前晶体透明),没有做到第一时间给出精准诊断。
我立马很惭愧,这位父亲锲而不舍年年报到,我也一直呵护,但我先入为主以为他女儿的白内障与手术有一定关系,虽然没有影响治疗,但没有在遗传咨询上做到位。这位父亲眼神里藏不住深沉的关切以及隐隐的担心,以前是对他的女儿,现在还包括对他的外孙,那个懂事、清澈、让人怜爱的男孩。我当然希望他们一切安康顺美,也希望一些与他们相似的患者,可以从中获得沉静平和与向前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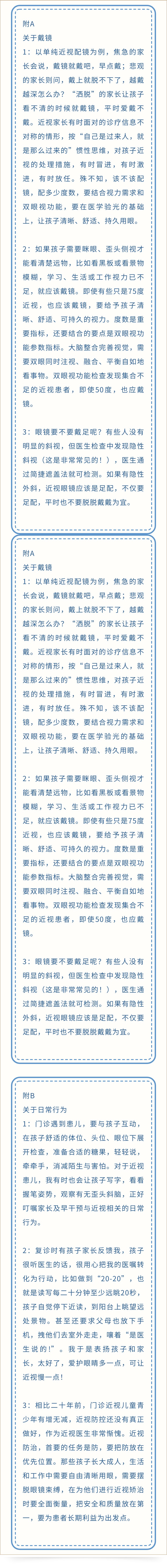
本文是周行涛版权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本文仅供健康科普使用,不能做为诊断、治疗的依据,请谨慎参阅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