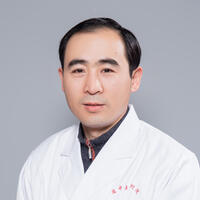 三甲
三甲
头痛---偏头痛
概念:头痛是临床常见的症状,主要分为3大组:原发性头痛;继发性头痛;脑神经痛、中枢和原发性颜面痛及其他头痛。偏头痛是原发性头痛中的一种常见病,是临床常见的反复发作的神经系统疾患,具有发病率高、高度失能的特点,压力、睡眠、情绪、环境、天气等因素容易诱发偏头痛的发生,会给患者带来沉重的疾病负担[1]。
病因病机:
1.西医病因病机:偏头痛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目前认可度较高的为三叉神经血管障碍学说、皮层扩散抑制(CSD)学说[2]。
1.1 中枢敏化与偏头痛:基于三叉神经血管障碍理论,多种触发因素作用促炎因子释放致中枢痛觉信号处理阈值降低从而引起中枢调节兴奋性和抑制性平衡能力的紊乱,继而三叉神经血管系统(TGVS)呈现敏化状态,进而呈现脑膜无菌神经源性炎症、肥大细胞脱颗粒、脑膜血管产生舒张变化等状态。而中枢敏化增加中枢神经元敏感性的作用,可能是通过影响突触可塑性、活化胶质细胞、降低伤害性信号传导阈值以及减少调节信号传递等途径得以实现[3]。
1.2 神经源性炎性反应与偏头痛:偏头痛患者痛觉系统下行通路障碍,会导致末梢神经P物质(SP)、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等促炎神经肽含量增多,进一步介导血管扩张、硬脑膜肥大细胞脱颗粒过程,促进细胞因子及其他炎性介质释放而致病[4]。CGRP作为一种强效扩血管的神经肽,参与中枢敏化,与偏头痛发作有着密切联系。分布在中枢的CGRP可激活神经胶质细胞,通过正反馈机制维持炎性反应及神经高敏状态;或通过强化中枢谷氨酸信号传导通路,继而增加突触可塑性、降低痛阈致敏[5]。另外,CGRP和CGRP受体在外周,有研究表明,急性偏头痛发作时外周的CGRP含量升高,故而抑制CGRP可能作为治疗偏头痛的思路[6]。
1.3 神经胶质细胞活化与偏头痛:偏头痛发病时,突触前神经元可释放出γ-氨基丁酸(GABA)和谷氨酸,它们起着维持中枢神经抑制性和兴奋性的作用,在被星形胶质细胞利用后,可产生谷氨酰胺,后者又成为供神经元内合成GABA或谷氨酸的前体从而调节疼痛[7];此外,三叉神经节中存在的星形胶质细胞,可通过释放TNF-α、IL-1β等炎性因子,维持敏感状态而引起疼痛[8]。小胶质细胞作为中枢神经中的巨噬细胞,活化后能促使IL-18、TNF-α等释放参与偏头痛信号传导通路[9]。小胶质细胞表面也可表达感知GABA和谷氨酸的神经递质受体,故而神经胶质细胞的活性,在维持和调节偏头痛病理过程中尤为重要。
1.4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以及核转录因子-κB(NF-κB)信号通路与偏头痛:MAPK和NF-κB是参与促发、维持甚至加重偏头痛的重要信号通路。c-Jun氨基末端激酶(JNK)p38MAPK通路被激活后可进一步激活其下游的c-fos、c-Jun。后者作为早期即刻基因,与痛觉调控相关,在偏头痛模型中被认为是中枢神经激活的标志[10]。NF-κB通过增加iNos、COX-2等炎症反应相关酶的转录,调节TNF-α、IL-1β、IL-6等炎症因子的表达,且作为重要的调节蛋白调控胶质细胞的增生、分化、免疫和凋亡,进而参与偏头痛发病过程[11]。
1.5 CSD与先兆性偏头痛:目前在细胞和动物模型中,基于一些单基因综合征,CSD被认为与先兆性偏头痛有关,它可触发脑部神经元和小胶质细胞去极化,而后去极化沿着皮层传播,导致TGVS的激活参与发病[12]。有研究表明,皮质中星形胶质细胞的非钙离子依赖性信号通路激活,在先兆偏头痛中也起着重要作用[13]。另外,谷氨酸能活性增加也被认为是产生CSD的关键因素,也是导致偏头痛的一种病理机制[14]。
2. 中医病因病机:偏头痛属中医“头痛”“头风”“脑风”“偏头痛”等范畴,头痛系统地分为外感和内伤两大类,外感风、湿、寒、热之邪,或内伤于阳亢、痰阻、瘀血、气虚、血虚或肾虚,阻遏清阳,壅滞经络,脉络不通或难以荣养,以致头痛。因此,不通则痛和不荣则痛是头痛发作的基本病机。若头痛长期反复发作,邪气日久入络,则可见风、火、痰、瘀、寒、虚诸多病理因素并存[15]。
临床表现:偏头痛临床代表性表现为单侧头痛,多呈搏动样反复发作,亦可伴随各种感觉失调、恶心、耳鸣、偏瘫、易疲劳感、颈部发僵、头皮疼痛等症状,一些患者病发前可伴有各种先兆症状[2]。
诊断与鉴别诊断:原发性头痛的诊断需要头痛达到一定的发作次数,符合相关的诊断标准且不能归因于其他疾病。偏头痛是临床经常遇到的原发性头痛类型,可与紧张型头痛和丛集性头痛进行诊断[16]。
1.初步判断头痛发作类型:
根据典型头痛发作的特点可初步判断头痛发作的类型,每一类头痛发作须同时满足时间特点、头痛特征、伴随症状方面的要求,表1是根据门诊病人病发时头痛的性质分析得出的[17],最常见的头痛类型是搏动样痛、针刺样胀痛、炸裂样痛、胀痛。如不经干预,通常头痛持续时间4-72小时;头痛常先兆或伴随出现恶心、呕吐;畏光、畏声。
2.明确诊断:
偏头痛:频繁的偏头痛发作会对患者的日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应予以重视。有先兆偏头痛和无先兆偏头痛是最常见的偏头痛类型。经历过5次以上偏头痛性头痛发作且不能归因于其他疾病,便可诊断为无先兆偏头痛。儿童偏头痛常为双侧头痛,多持续1~72 h,畏光、畏声症状可由他们的行为来判断。有先兆偏头痛的诊断主要依据先兆特点。偏头痛先兆指发生在头痛之前或伴随头痛一起发生的完全可逆的局灶性神经系统症状,主要表现为视觉、体感、言语、运动等的缺损或刺激症状,也可以表现为高级认知和意识障碍。在偏头痛发作前的数小时至1~2 d内出现,可表现为疲乏、注意力不集中、颈部发僵等前驱症状,这些症状并非先兆。许多有先兆偏头痛的患者也常有无先兆偏头痛发作。
3. 鉴别诊断:
3.1紧张型头痛:根据发作频率,紧张型头痛可分为偶发性、频发性和慢性等类型。每一型按颅周触压的疼痛敏感性又可分为伴颅周压痛和不伴颅周压痛两种亚型。颅周压痛可通过食指和中指在额肌、颞肌、咬肌、翼状肌、胸锁乳突肌、夹肌、斜方肌等部位小幅旋转或用力按压来判断,最好能使用触诊辅助设备。偶发性紧张型头痛是最常见的头痛疾患之一,但因程度不重,对生活影响不大,患者往往不来就诊。慢性紧张型头痛大多是由频发或偶发性紧张型头痛逐渐演变而来的,是门诊常见的病种。
3.2丛集性头痛:许多丛集性头痛患者会周期性地经历头痛反复发作的丛集发作期,而在其他时间没有头痛发作。丛集期多为2周至3个月。根据丛集期的有无和长短,丛集性头痛可分为阵发性丛集性头痛和慢性丛集性头痛两种亚型。有时丛集性头痛发作可以不很剧烈,不太频繁,持续时间也会较长或较短。有些患者可以只经历一次丛集期。
治疗:目前关于偏头痛的治疗在中医和西医上均有进展。
1西医治疗
1.1药物治疗:药物治疗是偏头痛最常见的治疗策略,分为缓解疼痛的急性治疗和减少发作的预防性治疗,包括非甾体抗炎药、麦角胺制剂、曲坦类药物、β受体阻滞剂、钙通道调节剂、抗抑郁药等,但这些药物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和局限,例如疗效欠佳、产生不良反应、出现药物依赖、患者依从性差等,长期的药物治疗还可能引起药物过度使用性头痛[2]。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在偏头痛的病理生理学中起到关键作用,它们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对比上述药物较高,近年来由此研发的抗CGRP药物被认为是偏头痛迈向精准治疗的重要节点[18]。
1.2心理干预治疗:心理行为干预可以改善睡眠、缓解疼痛。偏头痛是一种明确与精神情绪相关的疾病,且不可治愈,因此行为心理干预对偏头痛的防治尤为重要。目前,偏头痛的多种认知行为疗法包括放松训练、正念疗法、生物反馈,已在临床应用并被证实有效[19]。
1.3神经调控器具:针对外周及中枢不同神经部位的神经刺激已成为治疗头痛疾病的一种有前景的方式。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疗法基于电磁感应原理,磁场穿透颅骨后可产生一系列生理生化反应,对神经活动具有调节作用,且多项研究证明了TMS在偏头痛防治中的良好效果[20]。近年,不断有新的神经调控器具和方法应用于临床,其中颈部迷走神经刺激治疗偏头痛的疗效亦得到多项研究证实[19]。
2中医治疗:传统中医疗法防治偏头痛的独特优势在于在治疗策略上秉以“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理念,并灵活组合各种手段,包括针灸、艾灸、压穴、按摩、针刀、火罐等,做到个体化施治。在偏头痛发作期常以辨经论治为主,辅以辨证,非发作期则反之。其中中药也占一席之地,其治疗偏头痛的主要途径有传统方加减和中成药,临床上均有良好疗效。针刺目前与各类指南中推荐的一线药物相比,其预防性治疗偏头痛不论是长期疗效还是短期疗效,都具有相同甚至更明显的疗效,且不良反应更少[21]。国内外关于偏头痛的防治指南中也推荐针灸作为预防性治疗偏头痛的方法[22]。
预后:综上所述,偏头痛是临床常见一种疾病,患病率较高、确诊率较低,给患者及其家庭和社会带来极大负担。目前的偏头痛治疗方案因疗效和耐受性问题,尚无法完全解决疾病困扰。近年来,新型靶点药物的出现和非药物治疗包括传统中医疗法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患者的生活,可以更好、更全面地为患者提供适宜的选择,进而减轻疾病负担。
参考文献
[1] 尚成镇, 孔凡斌, 吴林, 陈春富. 偏头痛与躯体症状障碍共病现象. 国际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杂志. 2023. 50(04): 95-100.
[2] 王琳, 殷旭华, 杨挺嘉, 等. 偏头痛的发病机制及其治疗新靶点[J].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2023, 43(07):594-598.
[3] Hoffmann J, Charles A. Glutamate and Its Receptors as Therapeutic Targets for Migraine[J]. Neurotherapeutics, 2018, 15(2):361-370.
[4] Ashina M, Hansen JM, Do TP, et al. Migraine and the trigeminovascular system-40 years and counting[J]. Lancet Neurol, 2019, 18(8):795-804.
[5] Russo AF, Hay DL. CGRP physiology, pharmacology, and therapeutic targets: migraine and beyond[J]. Physiol Rev, 2023, 103(2):1565-1644.
[6] Iyengar S, Johnson KW, Ossipov MH, et al. CGRP and the Trigeminal System in Migraine[J]. Headache, 2019, 59(5):659-681. DOI: 10.1111/head.13529.
[7] Logiacco F, Xia P, Georgiev SV, et al. Microglia sense neuronal activity via GABA in the early postnatal hippocampus[J]. Cell Rep, 2021, 37(13):110128.
[8] Jing F, Zou Q, Wang Y, et al. Activation of microglial GLP-1R in the trigeminal nucleus caudalis suppresses central sensitization of chronic migraine after recurrent nitroglycerin stimulation[J]. J Headache Pain, 2021, 22(1):86.
[9] Gong Q, Lin Y, Lu Z, et al. Microglia-Astrocyte Cross Talk through IL-18/IL-18R Signaling Modulates Migraine-like Behavior in Experimental Models of Migraine[J]. Neuroscience, 2020, 451:207-215.
[10] Ramachandran R, Bhatt DK, Ploug KB, et al. A naturalistic glyceryl trinitrate infusion migraine model in the rat[J]. Cephalalgia, 2012, 32(1):73-84.
[11] Li Y, Zhang Q, Qi D, et al. Valproate ameliorates nitroglycerin-induced migraine in trigeminal nucleus caudalis in rats through inhibition of NF-кB[J]. J Headache Pain, 2016, 17:49.
[12] Levy D, Labastida-Ramirez A, MaassenVanDenBrink A.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meningeal and cerebral vascular function underlying migraine headache[J]. Cephalalgia, 2019, 39(13):1606-1622.
[13] Zhao J, Blaeser AS, Levy D. Astrocytes mediate migraine-related intracranial meningeal mechanical hypersensitivity[J]. Pain, 2021, 162(9):2386-2396.
[14] Chever O, Zerimech S, Scalmani P, et al. Initiation of migraine-related cortical spreading depolarization by hyperactivity of GABAergic neurons and NaV1.1 channels[J]. J Clin Invest, 2021, 131(21):e142203 [pii].
[15] 于明秀, 赵正超, 吕文学, 等. 偏头痛中医病因病机简况[J]. 实用中医内科杂志, 2019, 33(10):108-111.
[16] 头痛分类和诊断专家共识[J]. 中华神经科杂志, 2007, 40(07):493-495.
[17] 刘丽萍, 胡云峰. 神经内科门诊278例头痛患者临床分析[J]. 继续医学教育, 2014, 28(01):36-37.
[18] 姜威, 甘霖, 黄朔, 等. CGRP相关新型偏头痛药物研究进展[J]. 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 2019, 36(01):89-91.
[19] 安占军, 徐立霞, 史保权, 等. 偏头痛的神经调控机制及相关治疗进展[J]. 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 2022, 30(11):120-125.
[20] 贺麟媛, 潘永惠, 侯岳, 等. 偏头痛经颅磁刺激治疗的研究进展[J]. 临床神经病学杂志, 2023, 36(05):378-381.
[21]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医师分会,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头痛与感觉障碍专业委员会. 中国偏头痛诊治指南(2022版)[J]. 中国疼痛医学杂志, 2022, 28(12):881-898.
[22] 王文慧, 沈燕, 王舒. 针刺治疗偏头痛的机制研究进展[J]. 中国针灸, :1-11.
本文是陈永华版权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本文仅供健康科普使用,不能做为诊断、治疗的依据,请谨慎参阅





评论